詩詞鑒賞《唐宋五代詞·馮延巳·采桑子》馮延巳
馮延巳
昭陽記得神仙侶①,獨自承恩②。水殿燈昏③。羅幕輕寒夜正春。如今別館添蕭索④,滿面啼痕。舊約猶存⑤。忍把金環別與人。
注釋 ①昭陽殿:漢代宮殿名,漢成帝時趙飛燕居住于此。②承恩:得到皇帝的寵幸。白居易《上陽白發人》:“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③水殿:帝王乘坐的豪華游船。隋杜寶《大業雜記》:“(帝)敕王弘于揚州造樓船、水殿、水航……等五千余艘。”皮日休《汴河懷古》(其二):“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④別館:相對于昭陽殿的冷宮別苑。⑤舊約:舊時的愛情盟約。
鑒賞 劉永濟在《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中言:“此托宮怨之詞也。”則此詞以男子而作閨音,體現出“詞媚”的特點。這首詞借舊日承接恩寵的妃嬪之口,抒發詞人自己內心的愁緒,注重于內心世界,是和晚唐五代詞純情的特點氣脈相貫的。
詞的上半闋言昔日之恩情。第一句“昭陽記得神仙侶”,昭陽是漢代殿名,趙飛燕姊妹曾居住此。“舊愛柏梁臺,新寵昭陽殿。”(徐惠《長門怨》,在此惋惜班婕妤,感嘆趙飛燕)后代有以漢寓唐的風氣,所以在唐及以后的詩詞中,多有以昭陽私喻楊貴妃的,“昭陽殿里恩愛絕”(白居易《長恨歌》),“海上神仙字太真,昭陽殿里稱心人”(宋黃庭堅《調笑歌》)。不管這首詞中的“昭陽”是說趙還是說楊,總之,昭陽殿早已成為后宮爭斗的焦點,有著自己獨特的象征意味,成為獨承恩澤的名詞。“水殿燈昏,羅幕輕寒夜正春”是獨自承恩的具體表現,水殿中,羅幕后是帝王歡宴的場所。白居易《長恨歌》中“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專夜”,可作此句注腳。馮正中采桑子詞中三次用到“昭陽”,這里又明寫“獨自承恩”,也暗示著自己受南唐王朝重用,位勢顯貴的狀態。
詞的下半闋筆鋒一轉,直言今日幽怨。“別館”意指從大殿遷出,別置一館,和上闋“昭陽”相對,反映居住環境的變化。“蕭索”和“春”相對比,失寵后,人情淡薄,人煙蕭索自是常事,寫景滲情。舊時的約定杳無蹤跡,前日的恩榮快意化作今朝的滿面啼痕,反映了心境的失落。金環既是信物,又是后妃生子的標志。南朝宋雷次宗《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金環送給別人,恩寵則加與別人。兩個“別”字(“別館”和“別與人”)寫的是自己的出局,一個“忍”字,則在責怪君王的薄情負心,充滿了嫉妒與不甘。宋馬令《南唐書》記載:“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馮正中乃元宗近臣,可謂舊承恩寵,如今被斥責,心境自當與詞中后妃失寵有些許相通。景語皆情語,同樣寫怨詞也必有所怨之事,馮正中于南唐朝廷為重臣,仕途未經大風浪,然也有如此處所舉之不快,發之于詞。
這首小詞,雖然寫宮闈之事,少了香艷,多了清麗,“燈昏”“羅幕”“輕寒”等都有一種輕冷的味道,體現了馮詞“雅”的特點。(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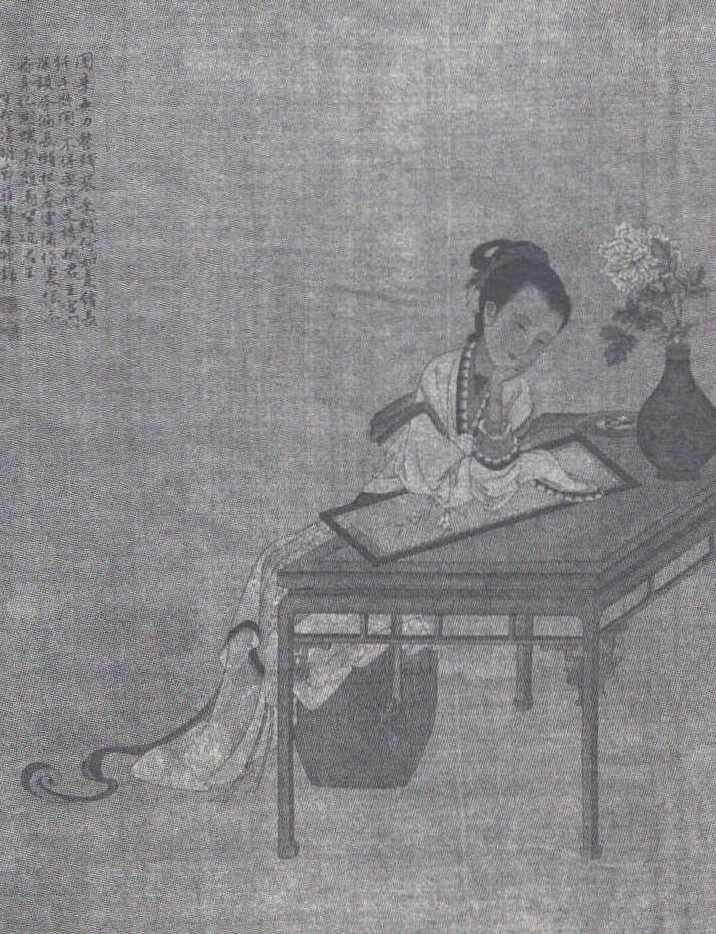
仕女圖 【清】 潘振鏞
采桑子
馮延巳
花前失卻游春侶,獨自尋芳①。滿目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
林間戲蝶簾間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②。綠樹青苔半夕陽。
注釋 ①尋芳:尋找春日的氣息,指游春。侶:同伴。②忍:怎能忍受。思量:想念,思念。敦煌曲子詞《鳳歸云》:“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誰為傳與書,表妾衷腸。”薛昭蘊《浣溪沙》詞:“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閑處暗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
鑒賞 據《詞譜》,《采桑子》本自唐教坊曲《楊下采桑》。馮延巳詞名《羅敷艷歌》,各詞家選延巳此詞,調均作《羅敷艷歌》。《四印齋刻本陽春集》仍題《采桑子》,共錄有詞作十三章。這十多章詞或謂情不能自已,相思到曉難忘;或謂托宮怨之詞;或謂暮年感舊,獨自低回,總之,“諸闋情采足媲《花間》,然玩其詞旨,流麗中有沉著氣象,實軼過之”(陳秋帆《陽春集箋》)。本詞觸景生情,通首寓孤悶之懷,“字正音雅,情味不求深而自深”(清陳廷焯《云韶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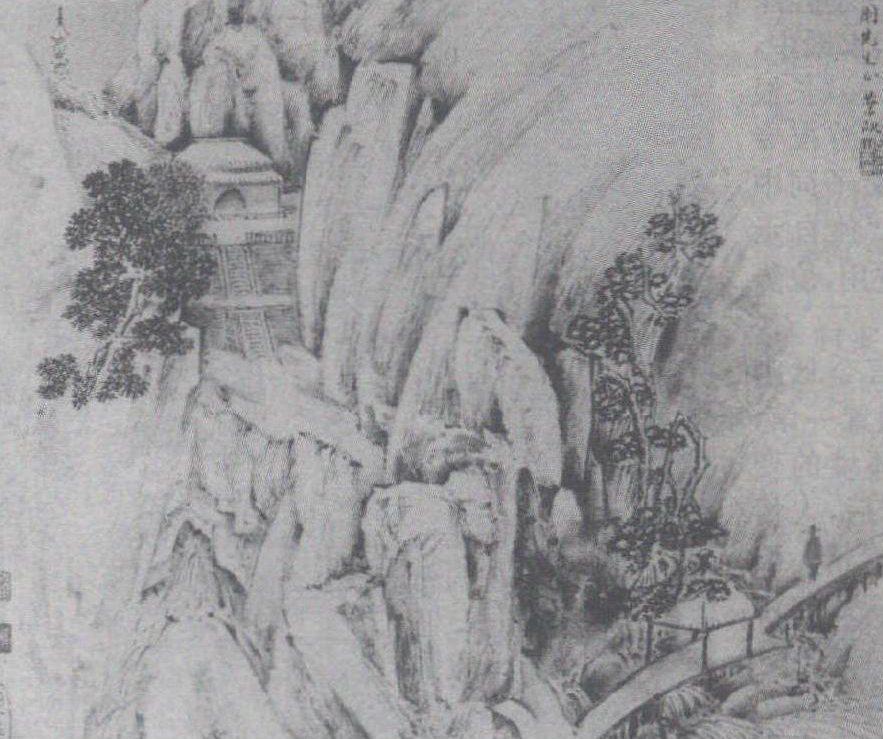
山水圖(之四) 【清】 葉欣 故宮博物院藏
上片寫獨自游春的悲苦心情。游賞爛漫春景,原是人生一大樂事,但因“失卻游春侶”,無人偕游,“獨自尋芳”,故反增凄涼:桃紅柳綠非但不賞心悅目,反而白白惹出傷春的情思;笙歌原來可樂,此時亦令人生悲。“花前”“笙歌”的春景是以樂襯哀的背景,滿耳歡愉的笙歌詠唱的是別人的快活,“縱有”二字從反面襯托了內心的悲愁。
下片寫自己形單影只,閑步四望,但見彩蝶雙雙,戲舞林間;春燕成對,簾間呢喃。這就更加激起了孤獨之感,黯然神傷。“綠樹”句以景結情,既與“滿目悲涼”呼應,又充分體現了馮詞偏“冷”的特點。夕陽斜照在青苔、綠樹之上,顯露出來的不是草木蔥蘢之暖氣,而是慘淡冷瑟的氛圍。依俞陛云之言:“江左自周師南侵,朝政日非,延巳匡救無從,悵疆宇之日蹙,‘夕陽’句寄慨良深,不得以綺語目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宋以后諸家詞論言及正中詞,大都認為其辭俊,其思深,其旨隱。究其原因,蓋“翁具才略,不能有所匡捄,危苦煩亂之中,郁不自達者,一于詞發之”(清馮煦《四印齋刻本陽春集序》)。若拋開政治上的功過得失來解釋這個問題,又必須看到作為一個杰出的詞人,馮延巳具備對于生活的高度敏感。縈繞在馮氏作品中的淡淡的哀傷其實來源于他對人生無常的思考。在馮延巳的其他《采桑子》中詞作中,“花前”“笙歌”和“雙燕”意象屢見不鮮。如“玉堂香暖珠簾卷,雙燕來歸”(中庭雨過春將盡),“獨立花前,更聽笙歌滿畫船”(馬嘶人語春風岸),“日暮疏鐘,雙燕歸棲畫閣中”(愁心似醉兼如病)。這些看似普通的場景、事物,無不承載著作者的新愁舊恨,然而他“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語還慵”(愁心似醉兼如病),故纏綿悱惻之情寓于藹然忠厚之言,若顯若晦,叫人深思。放眼五代詞壇,僅西蜀南唐為著,若推此時間詞壇健手,西蜀則韋莊,南唐則二主、馮延巳。再求風格高軼,含蓄蘊藉,堂廡特大,堪為宋人楷模者,則應推延巳。他為古典詩歌提供了一種“哀美”的范本。(劉玉潔)
集評 清·陳廷焯:“纏綿沉著。”(《詞則·別調集》卷一)
唐圭璋:“此首觸景感懷,文字疏雋。”(《唐宋詞簡釋》)



上一篇:《唐宋五代詞·和凝·采桑子》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下一篇:《兩宋詞·歐陽修·采桑子》翻譯|原文|賞析|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