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名嬙,為元代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中的女主人公。
王昭君,歷史上確有其人,《漢書·元帝本紀》、《漢書·匈奴傳》及《后漢書·南匈奴傳》均有記載。有關昭君出塞和番,漢代以后,詩、詞、曲及野史筆記、小說戲劇中多有所稱道,但就其形象之感人魅力而言,無疑當首推《漢宮秋》。
王昭君以美貌著稱,在古代四大美女之列。而《漢宮秋》中,其形象所以動人至深,除了“天生殊麗”之外,最主要的還在于形象本身所體現出的人情人性之美。這是一個美麗感人、溫柔賢慧、知情達理、善良純真的藝術形象。
王昭君出生在湖北秭歸三代為農的閭閻百姓之家。秀麗的山光水色養育了美秀如玉的王昭君。在恬靜沖淡的田園山村,她本能保持其如玉美質,度過其幸福的青春年華,沒有憂愁,沒有驚懼,沒有太大的希望,更沒有希望幻滅后的悲劇生涯。漢元帝的“選妃”,攪亂了她平靜的生活,一汪湖水激起了巨大的波瀾。王昭君以美貌入選朝廷后宮,但由于她不懂得人情世故,或者說由于她的過于天真純潔,不知道以重金賄賂朝廷命官毛延壽,遂被毛延壽在她的美人圖上點了破綻,使得她“一日承宣入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在冷宮中岑寂落寞地度過了十個春秋。
冷宮生涯,凄凄慘慘。雖地處繁華京都,卻無異于蠻荒地帶。缺少人煙,缺少陽光,沒有溫暖,沒有春天。孤寂的生活,對于一個正當豆蔻芳年的少女,該是何等的悲涼!愛情的追求得不到滿足,青春燃燒著的生命活力遭受到嚴酷的壓抑遏制,使得王昭君表現得近乎變態。為抒發郁憤愁思,她操起琵琶宣泄愁懷,未料竟以此邀來元帝駕幸。元帝的寵幸,使她欣喜激動,令她誠惶誠恐。她道是,“妾身早知陛下駕臨,只合遠接,接駕不早,妾該萬死”。元帝為她的才情傾倒,封她做了明妃,她又道, “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寵”。
一個是多情帝君,一個是貌美佳人。漢元帝與王昭君你貪我歡,恩愛纏綿,恨相見得晚,相識得遲。一日君寵,改變了昭君悲苦的命運,也改變了她的生活及宮中地位。昨日悲怨凄慘,今天盈盈笑臉。仿佛是嚴冬已過,春天來臨。春風和煦,陽光明媚,小鳥歌唱,生活是如此地具有詩情畫意。然而,昭君又何其不幸,其生也運偏奇,就在她正與漢元帝情意綿綿無盡期,相恩相愛難分離之時,晴天炸響了一聲霹靂,匈奴主呼韓邪單于聞說昭君絕色,率眾兵壓境,強索昭君為妃。此時漢國,勢已衰敗,滿朝文武, “只會文武班頭,山呼萬歲,舞蹈揚塵,道那聲誠惶頓首”。“養軍千日,用軍一時,空有滿朝文武,……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太平時,賣你宰相功勞,有事處,把俺佳人遞流。你們干請了皇家俸,著甚的分破帝王憂?那壁廂鎖樹的怕彎著手,這壁廂攀顛的怕破了頭。”文不能定邦,武不能安國,在這國勢直如壘卵之危,眼看漢祚難繼之時,王昭君請求和番之行。 “妾既蒙陛下厚恩,當效一死,以報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青史留名。”元帝也出無奈,允其請求。王昭君行至番漢界河黑江,縱身江中,為國殉生。歷史上演出了悲壯的一幕。
堂堂漢邦大國,面臨異族臨境,竟無人抵敵,而一弱閨女子,卻能為國分憂,知道去青史留名,這于一國須眉,該是何等的恥辱!而王昭君從大局出發,以國運為重,其見識氣度又是何等感人!當然,昭君和番,也擺脫不了士為知己所用的傳統命題,與報知己恩遇更大有關系,但其舍身為國之舉,其高風亮節,較之滿朝文武,又是極大的反差對比。古往今來,士人追求達官顯貴,立身揚名,名垂千古,其與昭君相比,不能不覺遜色,不能不覺慚愧。
歷史上的漢代,國勢頗為強盛,她擁有幅員遼闊的區域版圖,統轄了眾多的異族小邦。因此,王昭君出塞的背景,也絕不似《漢宮秋》中所寫的“空掌著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后漢書》記載: “時呼韓邪單于來朝,帝敕令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僉愿行。”可見歷史上的漢元帝,送妃子入番邦,并非出于無奈。而史書中的王昭君,其請使和番,只是為尋求個人解脫,也并非出于安邦定國,出于解民族之倒懸。在這里,昭君之舉,充其量只是不滿命運不公,為沖出牢籠進行了抗爭。其宮中不幸,所顯示出的社會意義僅有揭擿封建帝王荒淫無恥,后宮三千給廣大婦女帶來的不幸。而于王昭君,人們給予的頂多也只能是同情惋惜而已。《漢宮秋》改變了昭君出塞的背景及其和番的動機意愿,情況也隨即發生了變易。昭君不幸的人生變為悲劇的人生,人們也由對昭君不幸的同情變為對其崇高悲劇的贊嘆敬佩。
關于昭君的結局,《漢宮秋》對史書所載也作了很大的變動。《漢書·匈奴傳》記載,昭君出塞,受封“寧胡閼氏”,曾生一子。后單于死,其子雕陶皋繼立,求娶庶母昭君,昭君上書漢帝,欲不遂還國,漢帝令依胡俗,昭君又生二女。而在《漢宮秋》中,昭君出使,本出于無奈,而黑江殉國,則是為維護漢家尊嚴,不以帝王之妃,去做胡地之妾。她臨行前,“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絕不以“今日漢宮人”而去為“明日胡地妾”。顯見,昭君的投江殉國,不止為保全一己之人格完整,也是為維護民族尊嚴,免遭異族玷污。如此,昭君之品格內涵,也便有了質的升華飛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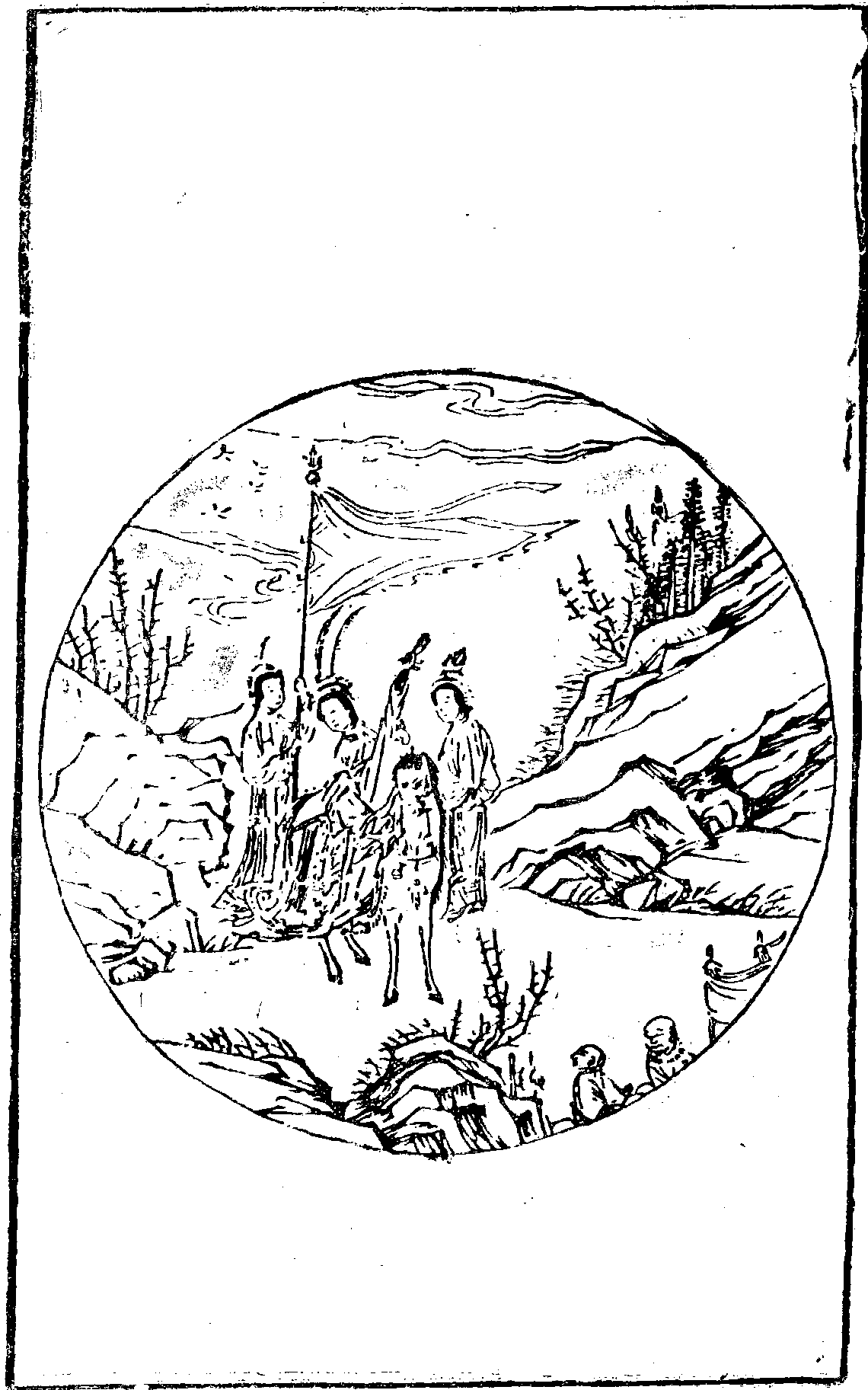
王昭君出塞和番
馬致遠變更了王昭君性格的涵蘊,傳達了民族思想情緒,但昭君形象卻也并不是作家愛國思想及民族情緒的概念衍化。這是一個立體多面,血肉飽滿,性格豐富的人物;決然出塞及黑江殉國,表現了她的壯烈陽剛,但她畢竟是一位弱小女子,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家女。在得遇元帝恩寵后,多次流露出綿綿之情,“妾與陛下閨房之情,怎生拋舍也!”“爭奈舍不的陛下!”真實地表現了一位青春少女對愛情的眷戀渴求。
在漫長的文學發展長河中,以昭君出塞為素材創作的作品多不勝數。而在一系列的昭君形象中,馬致遠《漢宮秋》中的王昭君又最為引人注目。在這里,昭君的悲劇,已不再是一種個人的悲劇,而成為時代的、社會的悲劇,昭君形象,也已由讓人憐憫同情發展為引人感佩崇敬。顯然,這是一個既血肉飽滿,具有鮮明個性,又具有普遍代表特征,包含著豐富的社會時代內容的“這一個”。凡此種種,均是《漢宮秋》中王昭君形象感人至深又千古不朽的重要因素。



上一篇:《王文瑞》文學人物形象鑒賞|分析|特點
下一篇:《王桂庵》文學人物形象鑒賞|分析|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