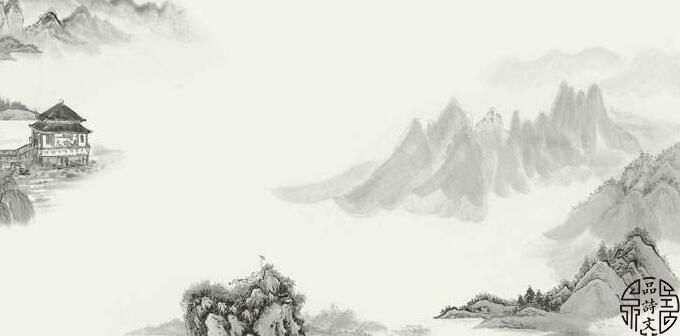
盛唐時期,經濟繁榮,國立強盛,涌現出大批稟受山川英靈之氣而天賦極高的詩人,形成“既多興象,復備風骨”的盛唐文化。李白就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和自信,狂傲的獨立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浪漫情懷,是成就其浪漫主義詩風的源泉。可以說,李白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繼屈原之后又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縱橫馳騁,騰挪變換,展現出一往無前的創造。在他的詩中,詩人將浪漫主義精神滲透于各種題材,浪漫主義精神情懷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高度的統一。詩人以他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和無可比擬的手筆極大地開拓了中國詩歌的藝術境界,豐富了詩歌的表現視野。可以說李白的詩歌是中國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照耀千古,永彪史冊。
李白的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的信念,使他有“濟蒼生安黎元”的抱負。這種理想成為他一生追求目標的基石。但“窮則獨善其身”思想不免與道家厭世的思想合流,游俠的思想又使他重諾輕物,輕視傳統,追求一種個性的張揚,養成狂傲不拘、飄逸灑脫的氣質和豪邁曠達的作風。這是魏晉開始以來人的覺醒發展至巔峰的產物,也是盛唐精神高度升華的產物。
李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老子的“無為”,莊子“無用”的思想,厭世、孤傲的風格在李白身上可找到影子。這種道家思想影響又有著雙重作用。積極的一面是狂放不羈、大膽追求、熱切的尋求個人自由與解脫。森嚴的封建禮法和庸俗社會關系使他窒息,黑暗的社會中找到出路,所以便采取狂放不羈的生活態度,急切的追求著個人自由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消極影響是表現頹廢避世的一面,一味地求山訪道、喝酒取樂、脫離現實,將道家那種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消極因素代入到他的詩中,無形中消弱了他的浪漫主義表現力和感染力。
獨特的經歷造就了獨特的思想,而獨特思想又造就了詩人獨特的性格。他們既有區別又有相通之處,在李白身上是不同程度地體現著。這就導致了李白思想的積極與消極、入世與出世、求仕與隱居思想行為的交織與融合。天地之道,得之于心,然后吐之為文章,這就是李白的詩歌。儒、道、俠三種思想奇妙地統一于李白思想性格和氣質中,這種獨特的思想使他的詩歌創作中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和極大地批判現實力量。
特定的文學是特定時代的反映,風格是時代的產物。李白乘時代之風,翱翔于詩壇,因而他的詩風完全打破了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變,達到了隨心所欲而變化莫測、搖曳多姿的境界,充分體現了盛唐詩歌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可以說李白積極浪漫主義風格正是盛唐氣象的反映,更重要的是當時詩歌是在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下形成的一種新潮流的產物,而李白也正是在這種文化乳汁的哺乳下步入了高峰,成為這種新詩歌的優秀代表。
李白的詩歌創作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主要表現為側重抒寫豪邁氣概和激昂情懷。他的詩常以奔放的氣勢貫穿,講究縱橫馳騁,一氣呵成,具有以氣奪人的特點。如《上李邕》:“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在這不凡的浩大氣勢里,體現出其自信與進取的志向和傲視獨立的人格力量。李白詩之所以驚動千古者正在于此。如他在《江上吟》詩中所說:“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杜甫稱贊他的詩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這種無比神奇的藝術魅力,確是他的詩歌最鮮明的特色。
唐詩發展到中唐出現轉折,由盛唐的浪漫熱情轉向對現實的冷靜思考,呈現出唐詩發展的第二次繁榮,而大歷時期正是盛唐向中唐的一個過渡,它開啟了中唐詩風的轉折。
李賀生活在中唐晚期,短暫的一生便經歷了德,順,憲宗三個朝代。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滿是失望的世界。頻繁的朝代更替,身居官職的身份,“往往獨騎還往京洛”的對政事的關注,讓他更深刻的體會到社會的黑暗,人民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尖銳矛盾。在這個籠罩著孤獨,傷感,憂郁的時代,李賀將自身浸潤其中,每一個細胞都吮吸著社會的乳汁,慢慢擴充,慢慢膨脹。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全部一股腦兒揮灑在文學的畫卷上,如山水潑墨畫般,隨意揮就,潑墨瀟灑,若隱若現間全是他飄逸的思緒和獨特的想象。他的苦悶,憂愁,壓抑,憤激,不滿,所有的情緒貫注在字里行間,滲透進詩的魂靈。于是,花有了語言,草有了思想,鬼蜮的世界開始生動上演,就連黑暗也有了楚楚動人的姿態。那種怪誕的詩風逐漸凝聚,籠罩在一個脫離了現實的世界上,李賀獨自陶醉其中。
李賀詩歌的怪誕,低沉,和當時的社會時代正相吻合,也體現了社會時代對李賀詩歌創作和藝術風格形成的影響。
中唐時期,大歷詩風盛行。較之盛唐時期的詩人,中唐的詩人失卻了盛唐詩人的昂揚的斗志,勃發的精神風貌。在經歷了社會的巨變后,他們追求太平的夢想落空,一切美景急速離場,換上的是一片枯槁。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創作心態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變得感傷而細膩,開始傾向于以個人的主管眼界去看待事物,剖析問題,謀劃創作。他們在夕陽衰草中抒發時運不濟的感慨,在長亭古道上徘徊尋找離去的方向。不忍直視破敗的社會,無言以對,促使他們尋求一個安逸寧靜的空間,以一種冷漠的眼光去抒發,去展現孤獨寂寞。難以言狀的內心世界。
中唐詩歌高潮到唐穆宗長慶時期逐漸低落。晚唐詩歌面貌再次發生變化。由盛唐的雄健壯麗,轉而為哀婉凄艷在這既延續中唐又能自成一代詩風的晚唐詩壇上,李商隱舉足輕重。
在詩歌創作上,李商隱開始時醉心于李賀那種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但大和九年的“甘露之變”,使他目睹朝官大量被殺,宦官擅權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轉變,寫下了〈有感二首〉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尤其是以七言律、絕為主體的大量無題詩和詠史詩,成為他最具獨特風格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說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詠史詩和無題詩的成功創作而奠定的。李商隱詩表現晚唐士人傷感哀苦的情緒,成就最高的是近體,尤其是七律、七絕。他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藉愛情遇合,于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征,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李商隱詩歌是心靈的象征,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
從李商隱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晚唐文學延續著中唐的路子,不過,由于甘露之變以后,宦官操縱時局,士大夫黨爭不休,藩鎮對抗朝廷,文人晉身權力中心的道路更窄,所以籠罩在文人心頭的是失望與沮喪的情緒。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晚唐人不僅沒有盛唐時代那種自由奔放的朝氣,也沒有元和時代那種滿懷激烈的勇氣。因此,這一時期的詩人,更多地是在對歷史的追懷中發出對現實的喟嘆,在對自然的眷念中表達對人世的疲倦,在對愛情的感懷中尋求個人心靈的撫慰。
晚唐詩人寫詩多是曠達之作,但這樣的曠達并非悠然自得的那種曠達,而是透露了對當時社會政治的不滿與失望,甚至是絕望。這樣深深的無奈,造就了杜牧的“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泊秦淮》)。”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淮》)。”這與魏晉詩風很是相似,同樣是多事之秋,也同樣對社會政治的不滿與失望,二者所采取的是很相似的手法。魏晉詩人醉心于玄學,而晚唐詩人則沉醉在歷史、自然和愛情的題材中。如三國時期“竹林七賢”之一嵇康的《幽憤詩》一樣,都是在述說本身的不得志和國家的曰薄西山。



上一篇:毛澤東詩詞的大美意象:豪邁、悲憫、宏大
下一篇:詩詞中的比興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