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蘇軾·八聲甘州》蘇 軾
蘇 軾
寄參寥子①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②。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愿謝公、雅志莫相違③。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④。
注釋 ①參寥子:僧道潛,字參寥,于潛人。北宋著名的詩僧。②“俯仰”句:王羲之《蘭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指世間萬事轉瞬之間就會物是人非。③“約他年”二句:用謝安典故,詳見第356頁《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一詞注⑤。這里指與參寥子約定他年重返浙東,不違歸隱杭州的夙愿。④西州路:《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后,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這里是寬慰參寥子不要為離別而悲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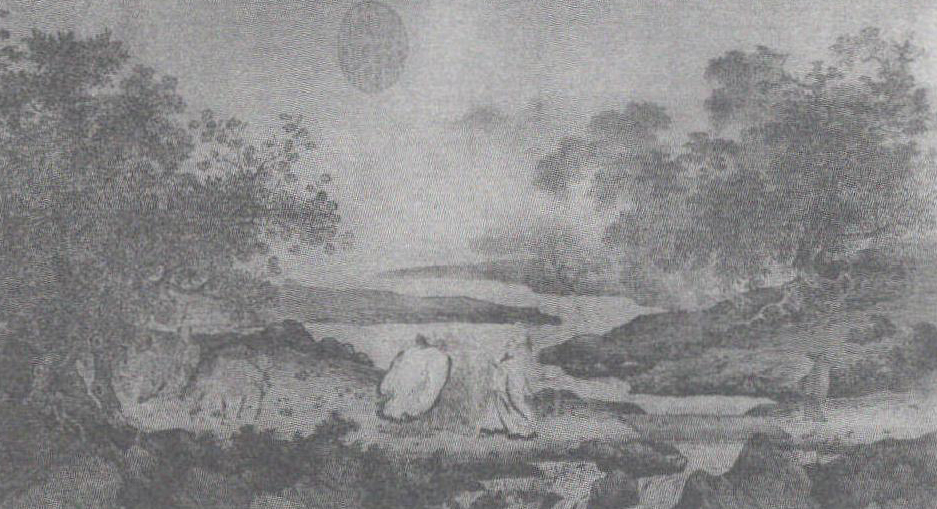
虎溪三笑圖 【宋】 佚名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鑒賞 蘇軾與參寥子之間的友情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一個是曾居高位,又名滿天下的文豪,一個是跳出世外,又才華絕倫的詩僧,地位的懸殊絲毫沒有阻隔他們知心的交往,在他們的詩文唱和中,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永遠的互相敬重和佩服。元祐六年(1091)蘇軾出知杭州兩年之后被朝廷召回,離別之際,寫下這首詞寄贈參寥子。詞的大部分都是在回憶兩人在杭州的生活,只最后幾句寫兩人日后隱居杭州的約定,并勸慰參寥子不要為暫時的離別而傷心。詞的結構非常平實,文辭也沒有一絲的奢華,然而情真意切,讓人回味無窮。
整首詞在錢塘江的大潮中開篇,“突兀雪山,卷地而來”(鄭文焯語),氣勢之磅礴,幾欲吞天噬地。一個“來”字、一個“歸”字,一個“有情”、一個“無情”,兩兩對比,把心中的思緒融入眼前的景色,混沌迷離,似有無限感慨,而又不可捉摸。前人曾用“覺天風海雨撲面而來”一語來形容蘇軾的“大江東去”詞,然而這首詞的第一句,似更當得起這種評價。全詞在一開始就達到情感的最高潮,接下來則是慢慢地回落,在回落中呈現波折。“問錢塘”三句似問非問,實際上只是抒發一種時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這一句本無甚奇特,但妙就妙在這些景物都包含著回憶。王國維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蘇軾這里寫景顯然也是為了寫情。“不用”二句是議論,語義上除重復上面幾句的感慨外,還表達一種“看破紅塵”的曠達,接著由這種曠達引入到“誰似”二句的自況,有一種自豪、欣慰之情。
轉到下闋,由“記取”二字引起回憶,作者著力凸顯景物的清空,這也是兩人品格、情趣的表現。接下來兩句的表達更加直白,情真意切,為最后的“勸勉”做好準備。謝安、羊曇的典故已見注釋,蘇軾首先是以謝安自比,表示自己不會忘記隱居杭州的夙愿,因此他與參寥子的分別只不過是暫時的。接著以羊曇比參寥,既說明兩人友情的深厚,同時也很典雅地勸慰友人不要過于哀傷。這里處處化用謝安、羊曇的典故,又句句緊扣作者自己與友人的感情,自然、貼切。
但是從字面上看,這兩個典故用得是不恰當的。謝安故事的最后是寫他將死之時,慨嘆不能得償夙愿,而羊曇也是在謝安死后才表示超常的悲哀。這似乎都不符合蘇軾和參寥當時的情況。所以后來有很多人說蘇軾這樣寫是“不祥”,因此引發了許多關于“詩讖”的討論。尤其是最后一句,在他們看來分明是蘇軾暗示自己此去必然九死一生,而勸慰好友不必學羊曇那樣悲哀。我們自然不相信所謂的“詩讖”,但也可以猜測,蘇軾此次回京,是否已經預料到了前途的兇險,做好了以死相爭的準備?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整首詞更可以作再深一層的分析、理解了。(姚蘇杰)
集評 明·沈際飛:“伸紙書去,亭亭無染,青蓮出池。”(《草堂詩馀正集》卷四)
清·鄭文焯:“突兀雪山,卷地而來,真似錢塘江上看潮時。添得此老胸中數萬甲兵,是何氣象雄且杰! 妙在無一字豪宕,無一語險怪,又出以閑逸感喟之情,所謂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者,詞境至此,觀止矣!”(《手批東坡樂府》)
鏈接 詩僧參寥子。隨著佛教的深入傳播和中國化,不僅中國的士大夫文人研習佛法,一些佛門弟子也多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詩文,由此產生了亦是僧人亦是詩人的“詩僧”。唐代著名的詩僧如皎然、靈澈、貫休等,其詩作至今流傳,成就頗高。至宋代,則有參寥子、慧洪等。其中參寥子與蘇軾有極深摯的友情,他曾不遠兩千里相從蘇軾于齊安,蘇軾貶謫海南時他也打算去探望,被蘇軾勸阻。有《參寥子詩集》傳世。



上一篇:《兩宋詞·柳永·八聲甘州》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下一篇:《兩宋詞·晁補之·八聲甘州》翻譯|原文|賞析|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