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法律·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歷史過程
中國傳統法律儒家化,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歷史過程。
(1)法律儒家化之權輿:《春秋》決獄。
《春秋》相傳為孔子修編的一部史書。孟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雖然可信程度有限,卻也表明《春秋》作為史書其“微言大義”的褒貶中樹立了善與惡的標準,具備了揚善抑惡、區分是非曲直的功能。
漢武帝采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一夜之間恢復了顯學的地位,儒家理論在官方的刻意扶持下,一躍而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圣經”。于是,充斥著法家精神的法律便面臨著一種空前的危機—精神依托及價值準則重塑之際,大規模重修法律不可能的前提下法律價值取向的危機。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無疑要求體現出官方的思想導向和精神追求,而當這種思想導向和精神追求完全附屬于儒家整體的價值體系之后,法家化的法律不僅不能滿足官方的要求,甚至是背道而馳。這一危機是隨著法家的式微,儒家的復興而到來,而《春秋》決獄便是當時官方與儒學大師們一起選擇的消除危機的辦法。
《春秋》決獄又稱為“經義決獄”,是指在司法審判中直接援引《春秋》及儒家其它經典的事例或精神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它的基本原則是“論心定罪”,所謂“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鹽鐵論·刑德》)。顯然,這是一條典型的主觀歸罪原則,而這種“善”與“惡”的認定不是依據事實或行為本身,而是以儒家經義的精神為準繩。一個事實或行為,從不同的觀念出發,立足于不同的價值取向,便會產生迥異的是非判斷,這便導致了所謂“疑獄”的大量形成。從漢朝以經義所決“疑獄”分析,大部分“疑獄”并非事實本身有什么可疑之處,而是如果按當時法家化的法律條文去審斷定罪的話,則與儒家倡導的精神原則有捍格可疑之處。在這種情形下,董仲舒及其追隨者在朝廷的支持下,毅然舍律就經,以儒家經義作為司法審判的準則,以圖借此扭轉法律中的非儒傾向,使儒家的精神原則率先貫注到司法活動中,并以此作為在法律領域徹底鏟除法家影響、實現儒家精神統治、促使法律儒家化的第一步,《春秋》決獄因之應運而生。
《春秋》決獄是儒家向由法家統治的法律領域發起總清算的第一步,作為一種盛行于漢朝、波及魏晉南北諸朝的司法現象,它對以禮入法這一決定中華法系本質特征的歷史演變過程有著開啟先河的作用,故《春秋》決獄乃是中國法律儒家化之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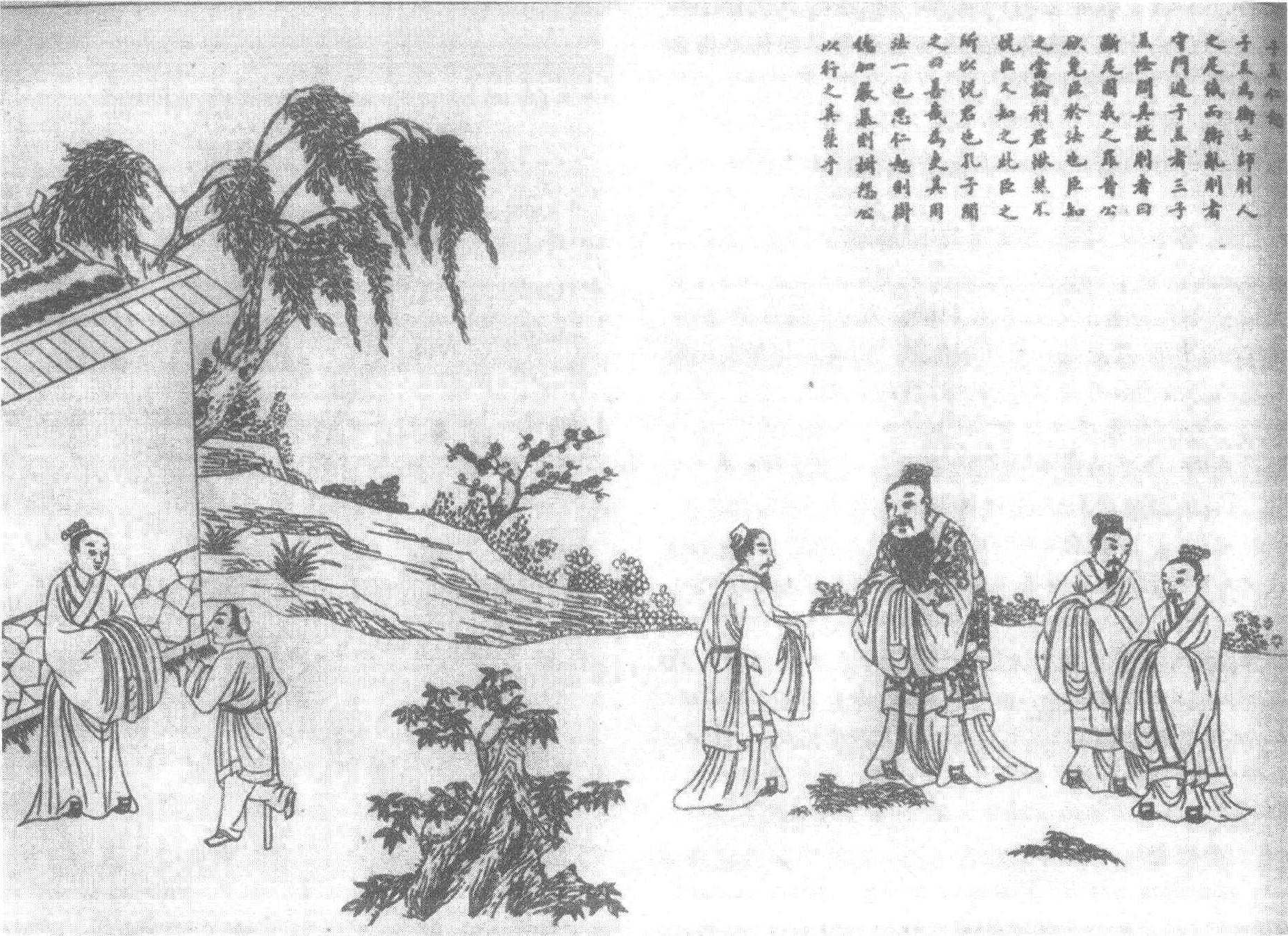
子羔仁恕(中華書局版《孔子圣跡圖》)
(2)法律儒家化之深入:以經注律。
以經決獄在官方的支持下得以蔓延,標志著儒家對司法領域的滲透已經取得了全面成功。但儒家的胃口并非僅及于此,他們早將目光盯在了法律本身,汲汲于全盤推翻舊律并樹儒家新律而后快。無奈“漢家自有制度”(漢宣帝語),大規模廢舊立新的條件也不成熟,加之漢之諸帝固循求安,并無大刀闊斧地改圖更新之志。于是,儒家只得另辟蹊徑,干起了注釋法律條文的事情來。
過去,儒家是不屑于直接與法律打交道的,故法律這塊領地多為法家所壟斷和世襲。而今,“法律之家亦為儒生”(王充《論衡·謝短篇》),風氣丕變,群儒鶩從。自西漢始,在引經決獄的同時,便有儒生聚徒闡釋法律,出現了“治律有家,子孫并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南齊書·催祖思傳》)的現象。引經注律在東漢掀起高潮,“后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余言”(《晉書·刑法志》),規模之浩大,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由此亦可窺諸儒注律的熱情之一斑。不過,熱得過分自然會造成泛濫,數百萬字的注釋只會令人更加無所適從,所謂“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于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余家”(同上)。最高統治者一方面認可了以經注律的行為,賦予其法律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規縮了范圍,僅承認鄭玄的“章句”可以在司法審判中予以引用的法律地位,這不失為一種明智而又現實的做法。
與《春秋》決獄一樣,引經注律的目的仍在于納禮入律。漢儒殫精竭慮,立洋洋數百萬言而樂此不疲,無非是為了將儒家學說的精義貫注到法律的每一條、每一字上,他們企圖在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從內容和精神上改法家之律為儒家之律。隨著他們注釋章句的被認可而具有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從實質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如今剩下的只是將軀殼更換的問題了。
(3)法律儒家化之完成:以經立法。
有了《春秋》決獄和以經注律的鋪墊,法律儒家化的條件已經成熟,只待歷史契機的到來,這一工程便會啟動。
這種歷史的契機,便是改朝換代。一當舊的權威與秩序被摧毀,總會激發出一種尋常少見的更法改圖的熱情與勇氣。漢家天下自東漢末分崩析離之后,漢家之律也隨之壽終正寢。魏、蜀、吳三國均懷更新法律之志,而其中尤以曹魏為甚。值得注意的是,創制魏律者,則已非儒生莫屬。陳群崇奉儒經,從其奏議動輒引經述義而觀之,碩儒之稱并不牽強。而劉劭更曾”受詔集五經以類相從,正始中執經講學”,又嘗“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易俗,著《樂論》十四篇”(《三國志·劉劭傳》),其精研經典,醉心禮樂,由此可見一斑。魏律正是出自此輩之手,這才成為儒家化法律的拋磚引玉之作。魏律儒家化的標志,便是“八議”之制正式入律。
同樣,晉律的撰訂者也不出儒生之列。據《魏書·刑法志》:“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條。”可見,由儒者依經制律,已成為國家定制。參與擬訂晉律的鄭沖、杜預、裴楷等果然無不碩學通儒,制律自然以儒學經典為圭臬,“竣禮教之防,準五服而治罪”(《晉書·刑法志》),立法指導思想已全盤儒化,促使條文內容又朝脫胎換骨的方向邁出了大步。
晉律在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而北朝的立法則是這一過程的高潮部分。北魏之主雖為胡族,卻對漢文化推崇備至,也深諳以漢法治理中國之理,故其創制立法,無不倚重中原人才。參與制訂北魏律的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劉芳之流俱為一代宏儒,經學之造詣,“擅美一時”。他們利用北魏統治者并不關心漢族祖宗制度法律的因革沿襲心理,肆無忌憚地大改法律,傾心竭力地將儒家禮教的精華全盤引入法典之中,從而令北魏律朝儒家化的方向發生了洗面革心的巨變。而北齊立法,則是以北魏律為藍本,所損益者無非在于加深儒化的力度。因為與前朝一樣,北齊律依然不外乎諸儒的嘔心瀝血之作。
至此,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已經基本完成,隋、唐所做的,只不過是將這一成果繼承與固定下來。所以近代史學巨擘陳寅恪先生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漢律復采之,輾轉嬗蛻,經由齊、隋以至于唐,實為華夏刑統不祧之正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各朝立法的一脈相承,不正是它們俱奉儒經為圭臬的必然結果么?!
《唐律疏議》是古代法典的代表之作,它集前代立法之大成,“一準乎禮,而得古今之平”(《四庫全書提要》),顯然也可表明其以經立法的本質。長孫無忌等主稿者在《進律疏表》中就曾以立法是在“網羅訓誥,研核丘墳”的基礎上完成而自炫。唐律的內容,“實三典之隱括”,儒家經義的精神,俱以禮的名義滲入到了條文之中。諸如“八議”、“十惡”、官當、存留養親、服制定罪等等最能體現儒家禮義精神追求的制度,均一一明載于律。更有甚者,長孫無忌等人還將以經注律的傳統發揚光大,創立了律、疏合一的法典體列,其初衷顯然在于讓刻板單調的律條洋溢出儒家活的精神,讓每一個司法者在援律量刑時體會到以經決獄的真諦。所以《唐律疏議》不僅是以經立法的結晶,更是整個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包括以經決獄、以經注律在內的一切有效手段、方式及成果的濃縮和再現。



上一篇:儒學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法家:“嚴刑峻法”
下一篇: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清代考據學:訓詁明則義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