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章太炎的建樹·近代“訂孔”的先行者
1901年,章太炎發表《訂孔》一文。訂者,平議,也就是重新評價之意。訂什么? 主要是糾正對孔子和儒學的不恰當評價。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不但斷言六經為孔所作,且論定孔子所以為大圣為教主,范圍千秋萬世,均因此故。章太炎出而力駁,“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女商事魏君也,衡說之以《詩》、《書》、《禮》、《樂》,從說之以《金版》、《六弢》。時老、墨諸公不降志于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章太炎認為,六經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故六經中的故事為老子、墨子所熟知。在秦始皇焚書以后,道、墨諸家日漸衰微,唯有儒家各類典籍“遭焚散復出”。因緣時會,孔子遂成為一位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究其實際,孔子的學說并不見得高明,比起孟子來,“博習故事則賢,而知德少歉矣”;比起荀子來,優絀長短更是昭然。歷代統治者尊孔抑荀,導致“名辯壞,故言淆;進取失,故業墮”,嚴重妨礙了中國的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訄書·訂孔》)。
在1906年發表的《諸子學略說》中,章太炎進一步從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對孔子加以全新的評價:“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在他筆下,孔子開干謁游說之風,是一“湛心榮利”、“嘩眾取寵”之徒。孔子倡導所謂“中庸”,馴致儒家道德水準難以上揚:“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昌設奔競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于函胡之地。”文章引《墨子·非儒》譏評孔子“窮于陳、蔡之間”的“汗邪詐偽”,直斥其為甚于“鄉愿”的“國愿”。文章還直揭“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在這里,章太炎把“大成至圣”的神圣外衣剝了個精光,把孔子徹底降到一般道德的理想水平。
不過,章太炎也并沒有全盤否定孔子。在他筆下,孔子以一史學家和教育家現身。《訂孔》堅持并發展了章學誠所提出的“六經皆史”的觀點,強調孔子刪定六經以保存古代典籍,為“古良史”。《諸子學略說》則肯定“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訂孔》贊揚孔子為有“三千之化”的教育家。《諸子學略說》也肯定其熱心教育、不信鬼神,“變幾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迥絕千古”。
對孔子及其儒學加以如此直截了當、毫無顧忌的批評,章太炎實為近代第一人。孔子和儒學在思想文化界的無上權威,使得前此康有為等只能用塑造一個“托古改制”的新孔子和形式上尊孔尊經的辦法,進行迂回戰。這位“孔教之馬丁路德”致力于在經學的殿堂內部發動“宮廷政變”,只能讓自己塑造的新孔子仍然穿著古色古香的舊服裝上場。章太炎則不然,他致力的是還孔子與儒學的本來面目,給孔子與儒學以實事求是的理性主義的新評價,強烈體現了一種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他自覺把引導人們沖破政治上的“保皇”關,同沖破思想上的“紀孔”關兩大任務合成一處。在他對古代孔子“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的批評中,不乏對以當代“素王”自居的康有為的針砭。他把孔子從歷代儒家尊孔論者的放大鏡下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之中,去其袞冕,撤其華蓋,這種認識具有更多的歷史真實性和可信性,也更富學術價值。這是必然的:章太炎從正面對孔子與儒學的凌厲攻勢,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傳統儒學文化的衛道士們痛詆他為“離經叛道”、“非圣無法”,進步思想界則肯定《訂孔》發表后,“孔子遂大失其價值,一時群言多攻孔子矣”(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
作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其學術起點及最大成就均在中國傳統文化。而他最初躍上學術論壇并引動學界注意,主要便在于他對以孔子和儒學為代表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加以廣泛的探討和初步的總結。在《訄書》修訂本中,除《訂孔》之外,他還新增了《學變》、《學蠱》、《王學》、《顏學》、《清儒》等篇,對漢、晉以至近代中國儒學文化的變遷大勢加以綜合考察。在表彰王充、王符、仲長統、崔實和顏元、戴震、惠棟等一批對儒學文化發展起過特殊作用的重要人物的同時,他也一反成說,批評那些歷來被視為儒學功臣的著名人物。他直斥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將儒學神學化宗教化,結果“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茍得利祿,而不識遠略”(《學變》)。在他看來,宋代歐陽修“不通六藝,正義不習,而瞍以說經”,蘇軾則專門“上便辭以耀聽者”,“令專己者不學而自高賢”,“使人跌飏而無主”。他們實開宋明理學和今文經學空言說經之濫觴,所以他不客氣地稱他們為“蠱民之學者”(《學蠱》)。明代王陽明的學說,“立義至單”,“獨‘致良知’為自得,其他皆采自舊聞,工為集合,而無組織經緯”(《王學》)。及至清代,“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清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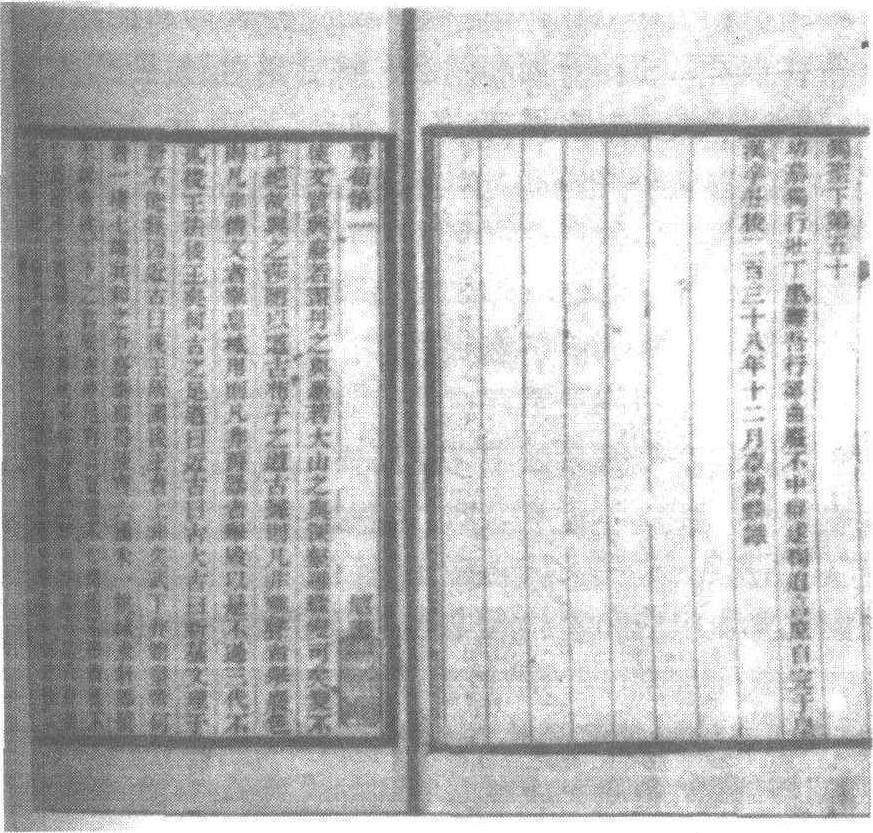
章太炎《訄書》(清光緒刊本)
章太炎目光如炬,縱觀千年,論析經史,品藻百家,校其異同,考其得失,顯示了近代思想文化界一代新人的虎虎生氣。他雄辯地證明,思想文化在永無止息的新陳代謝中前進,傳統儒學也是這樣,這正是歷史的必然。
需要指出,章氏此時所論雖在日后又被他自我否定,但他畢竟以空前的識力,發出空前的聲音。繼之而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驍將,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受過他的思想洗禮。作為運動中堅核心的《新青年》雜志七名編委中,竟有三名出自章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有兩名于當年章氏在日本暢發宏論時相與淵源(陳獨秀、沈尹默),另一名胡適,在他那部使他一舉成名、被稱為中國哲學史“開山”之作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不難發現章氏學術的影響。至于被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他之崇拜章太炎,不少批孔觀點得之于章氏著作,更不是什么秘密。



上一篇:近現代海外儒學概覽·亞洲·越南
下一篇:儒學與佛教·士大夫與佛教·近代思想家與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