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李清照·臨江仙》李清照
李清照
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①,予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蓋即舊《臨江仙》也。
庭院深深深幾許,云窗霧閣常扃②。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③,人客建安城④。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凋零。燈花空結蕊⑤,離別共傷情。
注釋 ①歐陽修《蝶戀花》原詞:“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②扃:關閉。③秣陵:秦改金陵為秣陵,即今江蘇南京。④建安:宋代屬建州,今福建建甌。⑤燈花:燈芯之余燼,爆成花形。
鑒賞 這首詞作于建炎三年(1129)初,是李清照晚期的代表作之一。《金石錄后序》載:趙明誠于此年二月,罷守江寧(今江蘇南京),三月,具舟上蕪湖,入姑蘇(今當涂),將卜居贛水上。本詞抒寫的就是趙明誠離開江寧之時李清照的憂傷心情,詞間彌漫著濃濃的離別情和家國恨。
小序交代了寫作緣起,起句直接采用歐陽修《蝶戀花》的首句“庭院深深深幾許”,連疊三個“深”字,不僅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收到了幽婉跌宕、回環復沓的聲情效果。接著帶出一筆“云窗霧閣常扃”,使讀者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了一個高樓形象,而且是云霧籠罩,縹緲朦朧。上句極言庭院之深,下句極言小樓之高,筆法奇矯,境界開闊,帶給人以無限的想象,而“常扃”二字,頓使這個高曠的空間變成封閉之所,色調也隨之蕭瑟、黯淡。“常扃”二字又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的“門雖設而常關”異曲同工,詞人內心的孤寂與惆悵之情躍然紙上。作者用語平淡,格調靜穆,雖未言人的愁苦,卻使人更難遣懷。
“柳梢梅萼漸分明”句表明女主人公偶然推開了窗子,早春的風光立刻撲面而來,放眼看去:柳梢的嫩芽正在萌發,梅花的葉萼逐漸清晰,原來,春在不知不覺中已悄然來臨。它催促著柳綠,催促著梅紅,催促著勃勃生機。這又是一個曼妙的春,本應與心愛的人一起攜手同游,飲酒賦詩,踏青訪古,熱鬧歡暢,但是丈夫即將離開,自己郁塞難排,縱使風光再好,她也無緒欣賞,辜負了東君的一片情深。
“春歸秣陵樹,人客建安城”二句繼續鋪墊,將詞人的傷感又推進了一層。秣陵,是南京,也是作者此時所居的地點;建安在福建,是丈夫離別后途經的場所,春歸人又去,相去萬余里。自己獨居閨中,孤單一人,丈夫漂泊在外,勞苦奔波。而這種悲劇又是誰造成的呢?作者沒有明言,但是那濃濃的怨恨已經使讀者聯想到凄涼、殘酷的“南渡”噩夢。
下闋開頭一句“感月吟風多少事”將作者的思緒拉回了往昔。那時她常和丈夫一起,在春風中賦詩,在秋月下填詞,花前柳下曾留下了他們親切交談、溫存浪漫的身影,銀色的月光中折射出了他們情投意合。而今一切都成追憶了,一句“如今老去無成”便使所有的回憶跌入了冷酷的現實中:濃情蜜意、滿腹才華、無限憧憬,都是枉然,國破家亡,親人離散,一切都已成空。正在傷心時,作者忽又拈出一句“誰憐憔悴更凋零”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郁、慘淡,“誰憐”猶言“無人憐”,只能任憑紅顏逝去,芳華消散。其實,丈夫趙明誠是珍惜愛憐她的,但是置身于那個山河破碎的時代,丈夫也是顛沛流離,身不由己。這句既是對自己韶華逝去的痛惜,又是對那個亂世的控訴,而“更”字又將這種愁怨加深了一層。

云山結樓圖 【清】 龔賢 廣州美術館藏
“燈花空結蕊”表明已是夜深,“離別共傷情”是她與丈夫惜別的畫面,“多情自古傷離別”(柳永《雨霖鈴》),“相見時難別亦難”(唐李商隱《無題》),都是極言分別的傷感和不舍。送行之時,人都是心情黯淡,索然無緒。作者沒有用“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柳永《雨霖鈴》),也沒有說“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王觀《卜算子》),但“共傷情”三字已經將綿綿的離愁宣泄殆盡,“共”字又暗示出此時二人都是愁腸百結,相依相戀,既有分別的苦痛,又暗含心心相印的深情,這與“一種相思,兩處閑愁”(《一剪梅》)的表達異曲同工。
南渡以后,李清照的詞風,從清新明麗,變為蒼涼沉郁,這首《臨江仙》是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準確編年的詞作。全詞語言平淡,色調沉郁,作者以如椽大筆譜寫出了國破家亡,夫妻分別的綿綿離歌,長歌當哭,攝人心魄。(張雅莉)
臨江仙
李清照
庭院深深深幾許,云窗霧閣春遲①。為誰憔悴損芳姿。夜來清夢好,應是發南枝②。玉瘦檀輕無限恨③,南樓羌管休吹④。濃香吹盡有誰知。暖風遲日也,別到杏花肥。
注釋 ①春遲:出自《詩經·豳風·七月》:“春日遲遲。”指日行漸緩,春日漸長。②南枝:南枝向陽,梅花先開。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③玉瘦檀輕:形容梅花開始萎謝。玉,比喻白梅。檀,比喻深黃色的檀香梅。④羌管:即羌笛,相傳為漢武帝時丘仲所制,長一尺四寸,因出于羌中,故名羌笛。羌笛中有名曲《梅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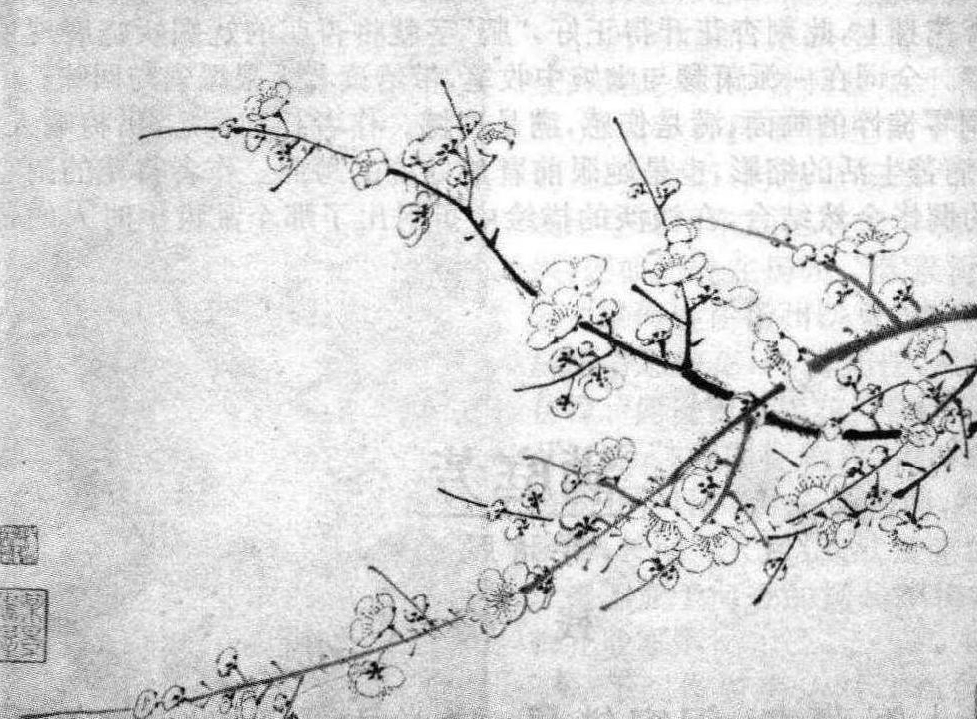
梅花圖(局部) 【明】 金俊明 上海博物館藏
鑒賞 在宋代,梅花是高雅之士風姿神韻的象征,也是世俗文人“附庸風雅”的手段。這首《臨江仙》也是梅詞,但側重點不同,梅花不是高潔趣味的寄托,而是傳情達意的使者。本詞作于建炎三年(1129),時已南渡,屬于李清照后期的作品,作者寫梅,更多的是抒寫家國之亡的悲痛,因此格調蒼涼,感情沉郁。
李清照在前一首《臨江仙》中有小序:“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予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蓋即舊《臨江仙》也。”可見這也是“數闋”中的一首。此篇起句又是直接采用了歐陽修《蝶戀花》的首句“庭院深深深幾許”。接著帶出一句“云窗霧閣春遲”,不僅點明了時間,而且交代了作者的居所環境。“春遲”,表明了此時風和日暖,春光正好;而“云”“霧”二字則表明小樓云霧籠罩,朦朧縹緲。
原來春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來臨,變換著天地,使萬象更新。“夜來清夢好”表明作者昨宵曾有佳緒,但夢是什么?作者沒有指出,接下來一句“應是發南枝”暗暗透露出她的夢中有梅花盛開的喜人風景,所以早晨起來,她迫不及待地去看小園之梅,看它們是否已綻放花朵、吐露清芬,但是一句“為誰憔悴損芳姿”就打碎了詞人的美夢,原來,梅花已經隕墮,早已失去了風姿神韻,她竟誤了花期,辜負了梅的一片情深,人會因惜花、憐花而傷感,作者卻問花“為誰憔悴”,造語新奇,惹人遐思。王維有一首《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描繪的也是寂寞之花,但是王維詩中的花是在“山澗”中,它自然是不容易被人看到,而作者筆下的梅是在庭院中,春光曼妙,梅花嬌柔,詞人卻絲毫沒有感覺到,直到花敗她才心痛憐惜,這就帶給人無限的追問,主人無心賞花,梅花憔悴而隕,貌似人無情,花有意,其實從側面襯托出了詞人的無緒心境,而這種無緒就是她南渡之后愁悶心情的寫照,而且這種愁悶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玉瘦檀輕無限恨”進一步寫梅花的凋零憔悴,看到這樣的殘梅,作者心中已經是悵然若失、心痛不已了,“無限恨”三字就是詞人此時最真實的懷抱,李清照在“雨疏風驟”之后,還會痛惜海棠的“綠肥紅瘦”,更何況是她鐘愛的梅花呢?此刻她陷入深深的感傷與自責中。可舊恨未平,新愁又生,南樓不知誰在吹羌笛,傳來了一曲哀怨的梅花曲,梅花本已凋零,更哪堪這凄愴的《梅花落》,難道它還要催促枝頭僅有的殘香?
“濃香吹盡有誰知”是梅的心聲,也是作者的呼喚,“有誰”猶言“無人”,連愛花的李清照都空負了花期,還會有誰憐花、成為花的知己呢?梅花只能在寂寞中開,在寂寞中敗,花美無人看,花香無人知。“暖風遲日也,別到杏花肥”更將這種傷感之情推向了極致,梅是春的使者,肩負著報春的責任,春本應是愛梅的,而此時它們也毫無留戀和憐惜,早已不再在意梅花的枯枝敗葉,而是把心思轉移到了杏花身上,此刻杏花開得正好,“肥”字就將杏花的嫵媚妖嬈展現殆盡,更折射出了梅的落寞清寂。全詞在一派蕭瑟與幽婉中收筆,帶給讀者無限思索與回味。
本篇寫梅,通篇全是梅凋零憔悴的畫面,滿是傷感,滿是遺憾。作者托物言志,借梅喻人,詞中的殘梅正是作者后半生痛苦生活的縮影,也是她眼前窘迫處境的寫照。作者將花的凋零與人的遲暮、花的孤寂與人的惆悵全然結合,在淡淡的描繪中折射出了那個亂世中時人的普遍情懷。(張雅莉)



上一篇:《兩宋詞·朱敦儒·臨江仙》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下一篇:《兩宋詞·陳與義·臨江仙》翻譯|原文|賞析|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