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劇曲鑒賞辭典·明代劇曲·明代傳奇·王光魯《想當然·赴塞》原文與翻譯、賞析
【一枝花】 (生冠服隨軍隊上) 北闕荷衣剛掛,陽關柳色方華。奉使虛傳司馬,他遙遙家舍即三巴,我遠山何處賒。
【北新水令】 萬重山腹都衣赭,最難堪早經圖畫。馬蹄行犖確,靴襖動森枒。慘可可烏紗,慘可可烏紗,倒是俺少年曾習弓馬,若不是呵,怎教這怯書生把天山射。(下) (凈扮守關將,眾隨上)
【南步步嬌】 荒煙處處迷官舍,一片長天掛。隴水咽悲笳,自幼從軍,鞍馬何曾下。某雁門將士迎接參軍,參軍爺將次到了,我們接遠些才是。今日里反面望京華,疑是功成放與歸田罷。(下)
【北折桂令】 (生上) 只說道半世里送斷嗟呀,那知屏中花鳥道是杯里弓蛇。當日個味后留佳,啖蔗從楂,誰想是艷苦匏瓜。又結果難查,只落得衣鐵披沙。說甚么風云叱咤,沒來由胡天玉節,耽誤了星漢銀槎。(下)
【南江兒水】 (軍士上)旟旐連云起,刀紋偃月華,擺列個人樣的旗槍架。飄飄冷葉飛殘壩,疏疏淡竹編茅舍。遠寺寒墻,紅謝絳績交叉,一個個兕文披掛。(下)
【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生上) 謾說道英雄氣兒女嗟,怎忘得無意逢人夜。想不出傷心話,收不轉肝腸掛。呀,謊離離兩下成虛咤,只落得遠迢迢索把音書罷,悲咽咽一似烏孫嫁。波喳劍影里浸寒花,波喳劍影里浸寒花。(下)
【南園林好】 (軍士上) 點青山一片明霞,為軍的半世無家。聽廝殺抖碎銀牙,怕秋砧烏啼夜,愁柳笛碧溪沙,愁柳笛碧溪沙。(下)
【北收江南】 (生上)(內哨響介)這哀音是葉碎蒹葭,還爭甚麟閣高聲價。那壁廂長旗大纛擁高牙,怎知我心旌一樣搖云掛。要把憂愁變做狠辣,反教俺淚如潮疊上江沙。(軍士上)
【南倖倖令】英雄撐白骨,壯士死黃沙。倚松林擺定材官甲,簇擁的望烏紗,簇擁的望烏紗。(見介)守關將士領本部人馬迎接老爺。(生)起來。本部多少人馬? (凈) 步兵、騎卒共有三千。(生) 將花名手冊開序明白,明日到代州衙門依次聽點。
【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 軍校每休咱做書生亞, 咱不是書生亞。剛腸素與邊風狎,不費些撐達。走掣電麒麟胯,指六花星辰舍,不日里幕徙陰沙。枕兵符氛消夷夏,抖天關猿啼鶴叱。又何須矯節兵借,也不用草書蠻嚇。洗兵戈銀河傾瀉,試干將倚天長掛。我呵,自有那神機鬼詐,安恁御他。呀,管教你唱凱歌在賀蘭山下。
【尾聲】英雄到此也難禁駕,忍斷了淚珠盈把,便做了震地撐天快那些。
《想當然》事本話本小說《國色天香·劉生覓蓮傳》,講述書生劉一春與孫碧蓮、勻箋主婢之間演出的才子佳人風流故事。會稽劉一春文武全才,因父母早亡,功名、姻緣兩俱未成。赴錢塘拜望老師趙思智時,在后園月下偶逢趙家甥女孫碧蓮和侍女勻箋,一見驚為天人。不久一春被父親故友金維賢留在府中讀書,再度與隨父孫莊借住金氏園庭的碧蓮及勻箋相遇,幾人對月盟誓,私訂終身。同住金府的耿汝和出于嫉妒,在金維賢面前出言詆毀一春。金維賢試探一春后,認定他品節無虧,遂趕走耿汝和。劉一春得中進士,已成相府門客的耿汝和設計將他派為代州僉判,兼攝雁門參軍。一春遠赴塞外,與碧蓮等消息隔絕。后耿汝和奸計敗露,一春被任為翰林院學士,往故地尋覓碧蓮主婢,卻已人去樓空,遂到錢塘探訪趙思智。時碧蓮一家因金維賢去世,已轉投趙府居住。一春與碧蓮及勻箋意外重逢,終于成就姻緣。這里的套曲表現了劉一春奉命出塞時的矛盾心情,此時的劉一春遠離愛侶和鄉土,既存著自傷飄零的悲觀情緒,又懷有建功立業的慷慨豪情,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態度在他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統一。
【一枝花】 和 【北新水令】 兩曲為劉一春的自敘之辭。【一枝花】 中引首的“北闕荷衣剛掛” 兩句以對仗形式要言不煩地交代了人物出塞的時間和背景,為下面的大段抒情作好了基本鋪墊。這里的 “北闕” 系指朝廷而言,“荷衣” 是平民的代稱,語出 《楚辭·離騷》 的“制芰荷以為裳”,“荷衣剛掛” 即表示舊時身份改變,出仕為官: “陽關柳色方華” 一語暗用唐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 詩中 “客舍青青柳色新” 等句的句意,以美好景色反襯出塞者遠赴邊地的孤獨與愁悶。“奉使虛傳司馬,他遙遙家舍即三巴,我遠山何處賒” 三句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中司馬相如奉旨出使西南夷的故典與劉一春當下領命出塞的現實情境相對比,借以突出劇中人遠行的悲苦情緒。劉一春暗自思量,前人傳言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是何等辛勞,但他世居巴蜀,到西南也就等于回了家; 而我現在卻要孤身出塞,山長水遠,前路渺茫,相比之下更是不幸得多了。曲辭中的 “三巴” 為巴郡、巴東與巴西的合稱,用來泛指四川巴蜀一帶; “賒” 在這里系語氣助詞,有趁韻的作用。接下來的 【北新水令】一曲開始具體描述劉一春奔赴邊關的艱辛旅程。“萬重山腹都衣赭,最難堪早經圖畫” 兩句正面描述沿途風景,“赭” 為赤紅色,“難堪” 有難以忍受之意。“萬重山腹都衣赭” 是以群峰身著赭色衣裝的比喻來描繪萬山紅遍的奇麗景象,這如畫的沿途風光使遠行者懷遠思人的綿邈意緒油然而生,不禁憂從中來,發出 “最難堪早經圖畫” 的深切感慨。“馬蹄行犖確,靴襖動森枒” 兩句進一步敘寫行路的情景。“犖確” 為摹繪山石嶙峋之狀的形容詞; “森枒” 義不詳,可能是指高聳繁茂的樹林。這兩句既是對仗,又是互文,實際意思是說人和馬一起 “行犖確”、“動森枒”,靴襖鮮明,一路趲行,馬蹄得得越經亂石嵯岈的山嶺,穿過陰森蔽日的密林。此時的劉一春回想前事,又是悲傷,又是慶幸。悲傷的是有了頭上的烏紗,就不得不任人差遣,離鄉萬里去忍受風刀霜劍的侵凌; 慶幸的是自己 “少年曾習弓馬”,到了軍前不至于如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那般一無用處。最后的 “慘可可烏紗” 數語中,“慘可可” 主要用來形容人悲憂的情狀,“怎教這怯書生把天山射” 一句則借用 《新唐書·薛仁貴傳》 所載唐朝大將薛仁貴 “三箭定天山”、威震西域邊陲的故事來代指劉一春出鎮邊關的行動,此句由于是出諸劉一春之口,故而言語中略顯自我嘲弄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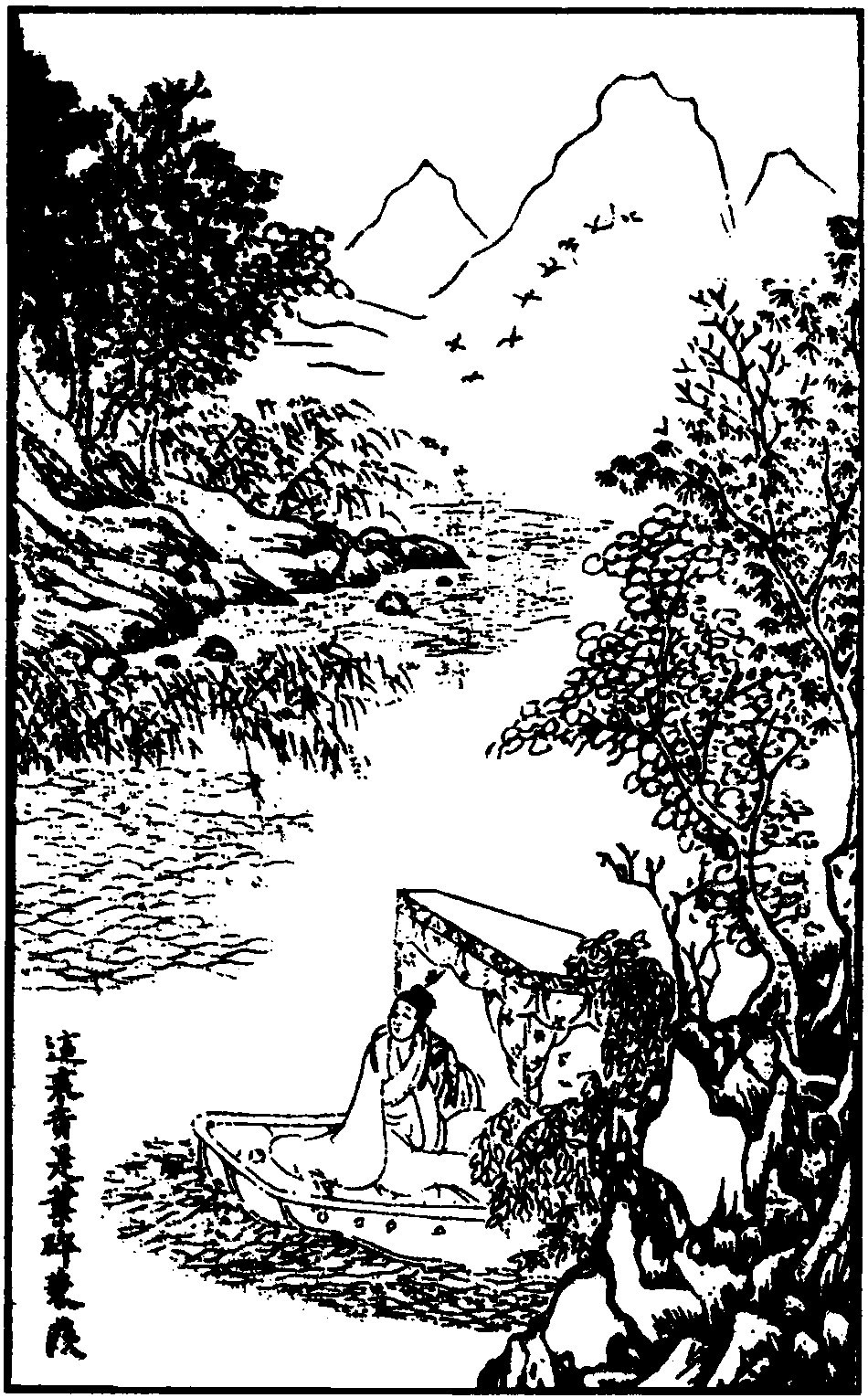
下面的 【南步步嬌】 一曲有意變換角度,從戍邊將士身上著筆,真實描摹他們餐風飲露的軍旅生活。“荒煙處處迷官舍,一片長天掛” 兩句以寫意筆法勾勒出邊地寥廓浩茫的自然環境,奠定了本曲及以下表現戍邊將士情緒諸曲的沉郁基調。邊關人跡罕至,沿途設置的官家驛站籠罩在荒野的煙霧之中,益見孤零。一片長天毫無遮攔地垂掛下來,與地面相接,構成了這個荒涼世界闊大而蒼茫的背景氛圍。隨后的三句緊承上文的悲涼情調,揭示了眾軍士久在戎行、遠戍邊地的苦悶心理。其中 “隴水咽悲笳” 一句暗用古詩 《隴頭歌》 中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的語意,以一個獨具匠心的 “咽”字將 “隴水” 和 “悲笳” 兩種事物巧妙地綰合在一起,這里的 “咽” 既是水聲的幽咽,又是笳音的嗚咽,更進一步看,水聲暗啞如笳音,笳音亦低沉似水聲,兩者同時存在于邊地生活中,自然而然在戍邊將士的心底融合為一。說到底,無論是水聲還是笳音,原都沒有感情可言,是人的主觀感受給它們罩上了 “悲” 的色彩。有了這種在長久戍守后生出的厭倦情緒,將士們出隊迎接劉一春時因 “反面望京華” 而產生出 “疑是功成放與歸田罷” 的錯覺也就無足為奇了。曲辭中的 “反面” 系轉臉、回首之意,“京華” 為京城的美稱,“疑是功成放與歸田罷” 意思是說大家懷疑這次京城來人是朝廷因將士們戍邊有功,特意派來宣詔讓眾人解甲歸田休生養息的。一個 “疑” 字寫活了戍邊將士迎接新任長官時希望與困惑兼而有之的心態,從而有力地反映出邊地境遇的艱苦和眾人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同時又為套曲中劉一春連綿不絕的憂思作了很好的陪襯。
接下來的 【北折桂令】 一曲重新回到劉一春身上,繼續表現他由遠遣邊塞而興起的怨艾之情。劉一春邊走邊想,自思自嘆。首句中的 “嗟呀” 意指因未能顯達而產生的哀嘆; “杯里弓蛇” 與 “屏中花鳥” 構成句中對,典出漢應劭《風俗通》書中所記杜宣事,杜宣飲酒時將映射于杯中的壁上彎弓誤認作是蛇,為此而抑郁不快了很長時間。“味后留佳,啖蔗從楂” 的 “啖” 意謂吃,“楂” 在這里當是指根梢;據劉義慶 《世說新語·排調》,顧愷之食甘蔗喜從尾部開始,而后逐步向上,說是“漸至佳境”,此處即暗用其語。“艷苦匏瓜” 的 “艷苦” 是極苦的意思,“匏瓜”出于 《論語·陽貨》 中孔子的名言: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結果難查” 的 “查” 系估量之意,“衣鐵披沙” 則是就投筆從戎,穿上鐵甲、沐風浴沙而言的。這幾句意思是說,原以為得中進士就可以揚眉吐氣,將前半生的不得意一掃而空,哪知道如屏風花鳥般明麗的前程中卻隱藏著杯弓蛇影那樣令人憂疑的東西;本覺得情形會像由尾至頭吃甘蔗一樣越來越甜美,誰又能想到該甜的偏偏變為苦,不但得不到重用,而且還被打發到偏遠的邊關,如一只系而不食的匏瓜那樣遭人棄置,只落得個棄文就武、頂風冒沙的下場,這樣的結果真是難以設想呵。此時的劉一春對于代州僉判和雁門參軍的新職并無興趣,更不具信心,在他心目中,塞外沙場的 “風云叱咤”、“胡天玉節” 的靖邊委任根本就無足輕重,只有 “星漢銀槎”才真正令人向往。“沒來由胡天玉節,耽誤了星漢銀槎” 兩句的 “沒來由” 意謂無緣無故,“胡天玉節” 是古代天子使臣持以為出使憑證的玉制符節,“星漢銀槎” 典出晉張華 《博物志》,其書記載,漢代曾有人乘木筏從海渚出發,居然一直航行到與之相通的天河; 后來又傳說這個乘槎上天者就是出使西域的漢代名臣張騫。曲辭將有關張騫的兩個故典聯系起來,表面上是說張騫奉使前往塞外,因人世的俗務而耽誤了乘槎上天的神仙事業,實則以象征和類比的方式表達了劉一春自己的思想,他認為遠赴邊陲的任命實際上是耽誤了自己立身廟堂的錦繡前程。
【南江兒水】 一曲復轉而表現戍邊將士的精神風貌,借助典型的景物描摹突出一種豪放中夾雜悲涼的集體情緒。曲辭前幾句寫出邊塞軍營旌旗蔽空、刀槍成陣的壯盛氣勢,其中的 “旟旐” 泛指旌旗,“刀紋偃月華” 是說將士手中的大刀形似月牙。“飄飄冷葉飛殘壩,疏疏淡竹編茅舍” 兩句以對仗形式來描繪邊地景物,借以點明節令,渲染氛圍。落葉殘壩、竹籬茅舍和遠寺寒墻,共同構成了將士們活動的人世環境。接下來的 “紅謝絳績交叉,一個個兕文披掛” 兩句重點勾畫眾將士的裝扮,其中的 “紅謝絳績” 義不詳,疑 “紅謝” 同 “紅射”,“絳績” 同 “絳幘”。“紅射” 可指紅色的射鞲即射箭所用的臂套; “絳幘” 原為古代宿衛之士所戴的紅色頭巾,這里借以指稱戍邊將士的頭盔; “交加” 為錯雜的意思; 一說“紅謝絳績交叉” 是指 “遠寺寒墻” 紅色斑駁脫落的衰頹景況; “兕” 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猛獸,古人喜在鎧甲上鑄刻兕形圖樣以寓勇猛無敵之意,這種圖樣即是曲辭所謂的 “兕文”。這兩句與 “旟旐連云起,刀紋偃月華,擺列個人樣的旗槍架” 等曲辭相應和,于衰颯、清冷的背景上凸顯出戍邊將士的雄姿英風,成為套曲悲戚幽怨的情感底彩上第一筆醒豁的亮色,為后面昂奮高亢的抒情段落伏下了另一條情感線索。
隨后套曲重新轉入憂郁的情調,在傳達過劉一春遠離家鄉的感傷和功名不稱心的怨嘆之后,又通過一曲 【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細膩地展示他苦澀纏綿的相思之情。曲首的 “謾說道英雄氣兒女嗟,怎忘得無意逢人夜” 兩句意思是說,不要說我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像那個與孫家小姐碧蓮和侍女勻箋在月下偶逢的良宵我又怎么能夠輕易就忘掉呢。句中 “謾” 同 “漫”,相當于莫、休之類的意思; “兒女嗟” 意謂因兒女之情而嗟嘆傷懷。以下數句語勢流暢,一氣貫注而下,道盡了相思之苦與分離之痛。劉一春憂患頻經,悲凄到極處,欲說傷心話而想不出從何說起,欲拋卻煩惱又止不住對意中人牽腸掛肚的思念。落得這樣一個兩地相思、各懷悲嘆的結果原非其當初意計所及。眼下水遠山長,音訊不通,終是無可奈何。曲辭中“虛咤” 的 “咤” 意謂悲傷、慨嘆; “索把音書罷” 的 “索” 則有必須之意; “烏孫嫁” 一語典出 《漢書·西域傳》,烏孫為古代西域國名,漢武帝時曾以公主嫁入烏孫國去和親。這里劉一春因遠赴邊關,與心上人分離,故自比為哭哭啼啼被迫遠嫁的漢代公主。“波喳劍影里浸寒花” 中的 “波喳” 同波查,系感嘆詞。這兩句重復唱嘆,將沙場劍影與邊地寒花相映照,再次以象征的方式突出了人物孤苦無依的心境。
下一曲 【南園林好】 又轉為戍邊將士的詠嘆。曲辭借 “點青山一片明霞”、“秋砧烏啼夜” 和 “柳笛碧溪沙” 等色調清明的畫面來映襯他們苦守邊疆、“半世無家”的心靈苦悶及 “聽廝殺抖碎銀牙” 的厭戰情緒,形象生動,簡練傳神。句中的“砧” 是古代用來捶洗衣物的搗衣石,“碧溪沙” 則是柳笛中吹出的樂曲。這兩句的意思是說,烏啼之夜遙聞遠處的搗衣聲,便想起家中因思念而同樣難以入睡的親人;軍營之中聽到柳笛吹奏的 “碧溪沙” 曲,鄉情更加難以遏止。曲辭在表達這種種深沉的情感時不事鋪張,只用 “怕” 和 “愁” 兩個字來含蓄地點明一切,凝煉之中,別具耐人品鑒的意味。
再下一曲 【北收江南】 敘寫劉一春抵達邊關、遠遠望見軍中大旗時復雜的內心活動。“這哀音是葉碎蒹葭” 句緊承上曲的 “愁柳笛碧溪沙” 而來,令眾將士引發鄉愁的塞上之音同樣深深地打動了劉一春,在他聽來,這種凄哀的音調與秋天蒹葭葉碎的聲響一樣,使人聽來備感心灰意冷,連一向渴求的功名前程此時都覺得毫無意義了。面對塞外景象,劉一春止不住心旌搖曳,情緒激烈變動,雖已打定主意在將士們面前收斂愁容,表現一點新官上任的威勢,但一時之間,眼淚卻還是難以控制地流瀉而出。由灰心喪氣到動蕩不定,由立意鎮靜到哀傷轉甚,曲辭將人物的心理變化描摹得層次分明而富于辯證色彩,讀來真切可感。曲中 “麟閣” 為 “麒麟閣” 的略稱,因漢宣帝曾在麒麟閣上懸掛十一功臣像,以表彰其功勛,故后世以“麒麟閣” 作為功名勛業的代稱; “那壁廂” 為那邊之意; “高牙” 的 “牙” 意為大旗,與 “長旗大纛” 同義,都系指大將的牙旗。
進入【南倖倖令】 和【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 兩曲以后,曲辭的風格隨著人物心緒的調整而相應發生了改變,由原來的抑郁感傷一變而為雄強勁健,呈示出與兒女情長截然不同的陽剛之美。此處的【南倖倖令】 屬過渡曲,主要用于收結以上戍邊將士的系列抒情段落,引發劉一春下面的大段慷慨陳詞。“英雄撐白骨,壯士死黃沙”兩句以精嚴工整的對仗涵括了 【南步步嬌】、【南江兒水】 等曲的內容,而“倚松林擺定材官甲” 以下數句則交代了將士們迎接劉一春的地點和陣勢。這里的“材官” 是武卒或下等武官的通稱,“烏紗”借來代指奉命履任的劉一春。在戍邊將士整齊的軍容和雄健氣勢的感染下,劉一春暫時拋開了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激起一腔豪情,預備和眾將士同甘共苦,在邊塞建立功勛,因而以飽滿的熱情和輕快的言辭來激勵眾人的斗志,【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 發攄的就是這種豪邁樂觀的情緒。曲辭中意同看, “書生亞” 意謂文弱書生一類的人物; “狎” 有習慣、 親近之意,“剛腸素與邊風狎” 即等于是說自己對于邊地的艱辛早有體會,毫不在乎; “撐達” 在這里有顯本領的意味,“不費些撐達” 意謂堅守邊關輕而易舉,不必花多少力氣、用多少本事。“走掣電麒麟胯” 三句以長官口吻安排了遷徙軍營的任務。句中“麒麟” 借以指代將士的坐騎,“走掣電” 是形容其奔走的迅捷; “六花” 系雪花的代稱,“星辰舍” 為天空; “幕”則是指軍營帳幕。這幾句意思是說近日內軍伍將遷徙他處,全軍要頂風冒雪,疾速行進。以下四句連用多個與軍事和邊防相關的典故來表示守邊御敵的必勝信心。“枕兵符氛消夷夏” 中的 “兵符” 指兵書; “氛”意指兇險的兵氣; “夷夏” 為漢人和少數民族國家或部落的合稱。全句意思是說有兵書在手,朝廷與異族的爭戰指日可勝,迫人的兵氣即將消除。“抖” 有振作之意;“天關”代指地勢險要的關隘; “猿啼鶴叱” 典出晉葛洪《抱樸子》,據該書記載,
周穆王南征,三軍盡皆化為異類,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沙;這里借用此典,以猿、鶴喻指忠于朝廷的戍邊將士,“猿啼鶴叱” 也即成為將士英勇的比喻說法。全句意謂將士們鎮守邊關,勇不可當。“矯節兵借” 一語典出 《史記·魏公子列傳》,魏公子信陵君為救援遭秦兵攻打的趙國,設法盜得調兵的符節,矯魏王之命,發兵解了邯鄲之圍; “又何須矯節兵借” 句反用其意,表示手中擁有朝廷特授的統兵大權,因而不必如信陵君一般矯節借兵。“也不用草書蠻嚇” 句明用李白的傳說故事,據說李白能通外邦語言,曾為唐玄宗起草答渤海國可毒書,打消了其不臣之心,這封書信后即為人稱作嚇蠻書。這里活用此典,宣稱有了固若金湯的邊城關隘,異族決不敢像唐玄宗時的渤海國可毒那樣猖狂挑釁、以無理要求脅迫朝廷。有了以上這些意氣昂揚的表白,曲辭緊接上 “洗兵戈銀河傾瀉,試干將倚天長掛”兩句也就顯得頗為順理成章了。這兩句化用了杜甫《洗兵馬》詩中 “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 和宋玉《大言賦》 中 “長劍耿耿倚天外” 的句意,說要用銀河之水洗去塵世的戰氛,讓寶劍倚天垂掛,威鎮天下,而不復在戰場上砍斫廝殺。句中 “干將” 是春秋時的名劍,“倚天” 為靠著天之意。兵止戰息,長劍閑置,貌似浪漫的曲辭中寄寓著渴望和平的平實理想。最后的 “我呵,自有那神機鬼詐,安恁御他。呀,管教你唱凱歌在賀蘭山下” 數句,“神機鬼詐” 意同神機妙算; “安”和 “御” 都有平定、駕御、控制的意思; “恁” 意為你,和 “他” 一起指代犯邊的異族; “你” 系指戍邊將士而言; “賀蘭山” 為西北山名,這里借以指稱邊地。這幾句與前面的 “枕兵符氛消夷夏” 遙相呼應,平穩地收住 【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一曲。
【尾聲】 再度回應前面的憂傷情感,表現劉一春激情過后復感凄楚卻又不得不強自抑制的悲涼心態。曲辭中的 “禁駕” 同禁架,為把握、控制之意; “忍斷” 即忍住; “便做了震地撐天快那些” 意思是說告別家鄉、遠離意中人,即使事業勛名驚天動地,又有什么值得高興的呢。這三句使整套曲中人物情感的發展變化在結尾時又添一波折,益見出作者文心之曲和功力之深。
全套曲句式整散結合,節奏快慢相濟,語辭文白夾雜,典故雅俗兼備,頗得元曲的韻味。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逸品》 給《想當然》 所下的考語為 “時出俊爽,才情迫露”,從以上套曲來看,這個評價大體不差。刊印本《想當然》前托名盧柟的《本敘》稱述此劇在創作上具有 “情自我生,境由他轉” 的特點,這一點也可在上選套曲中得到印證。值得一提的是,這套曲文南北相間,且特意用勁健的北曲來突出主人公劉一春的幽微心事,而以婉約的南曲為意緒蒼茫的戍邊將士寫照傳神,這種處理法與一般作者是略有不同的。它使得戲劇情感與曲體情感之間構成了剛柔互補的關系,既借助北曲弱化了主人公的悲傷情緒,使之與后面的激昂段落不致太過脫節,又通過南曲消減了將士們身上的剛猛之氣,使套曲的整體格調與情致基本上前后相若,保持著大體的均衡。



上一篇:《驚鴻記·梅妃宮怨》原文與翻譯、賞析
下一篇:《意中緣·會真》原文與翻譯、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