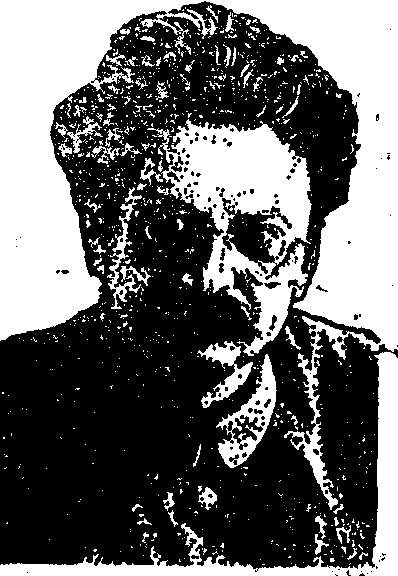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原姓勃朗施坦(Вронщтейн),聯共(布)黨內反對派首領,國際范圍具有很大影響的機會主義代表人物。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俄歷)生于南俄草原揚諾夫卡一個富農家庭,祖籍是猶太人。童年是在閉塞的鄉間度過的。揚諾夫卡離郵局、鐵路線都很遠,離世界重大事件的策源地更遠,惟有世界市場上谷物價格的漲落影響著他家的經濟收入。鄉間沒有中學,1888年,他進敖德薩圣保羅實科學校讀書。1896年轉學尼古拉耶夫,讀完七年制中學課程。據托洛茨基自稱,1895年以前,他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中學生,恩格斯逝世時,他連恩格斯的名字也未聽說過。
1896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的開端。他在尼古拉耶夫讀書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組織“南俄工人同盟”,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1898年,由于“南俄工人同盟”案發,被沙皇政府逮捕,判處流放西伯利亞東部4年。1900年,他在流放地開始為伊爾庫茨克《東方評論》撰稿。1902年秋,從西伯利亞脫逃,護照上用的名字為托洛茨基,此后一直沿用這個名字。逃出流放地后,他在薩馬拉參加了《火星報》組織,筆名“比羅”(意為“筆尖”)。后經蘇黎世、維也納、巴黎,于1902年底到倫敦,并在這里同流亡國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列寧、普列漢諾夫、查蘇里奇、馬爾托夫等首次會面。1903年起,他列席《火星報》編輯部會議,無表決權。他曾經是一個激烈的火星派分子,一度被人稱為“列寧的棍子”。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亞代表的身份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討論黨章時,托洛茨基屬于孟什維克,他以列寧的黨章第一條不足以防止機會主義,反而會使工人和知識分子“處在不平等的條件之下”為由,反對列寧的條文,贊同馬爾托夫的條文。會后,他加入孟什維克的“少數派委員會”。1904年,他退出孟什維克。此后,他長期游移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沒有任何明確的立場,……在各派之間任意飛來飛去”①。這是托洛茨基政治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
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國,在彼得堡活動。 5月遷居芬蘭。10月全俄政治總罷工的高潮中,他重返彼得堡,與帕爾烏斯合編《俄羅斯報》,與孟什維克合辦《開端報》,并參與彼得堡蘇維埃機關報《消息報》的編輯和撰稿。這些活動使他獲得較大的名聲。12月,彼得堡原任蘇維埃主席赫魯斯塔廖失被捕,托洛茨基被一度選為彼得堡蘇維埃主席。莫斯科12月武裝起義失敗后,反動勢力加強,他再度被捕,判處終身流放。
在1905年革命期間,托洛茨基開始形成他獨特的“不斷革命論”的觀點。這些觀點集中地體現在1906年他獄中所寫的《總結與展望》一書中,后來他對這些觀點不斷有所補充和論證,成為托洛茨基一生活動的主要理論基礎。托洛茨基后來把“不斷革命論”,歸結為“三個互相聯系的思想”,即:第一,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第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第三,國際革命的不斷性。
托洛茨基指出當時俄國革命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解決土地問題,革命第一階段的性質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在俄國,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也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唯一能領導革命的是無產階級。他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掌握了革命的領導權,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政權以后,一方面去完成歷史賦予的民主革命的全部任務,另一方面又不能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限制,必須及時將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由此,他宣揚帕爾烏斯提出的“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的口號。根據托洛茨基的解釋,所謂“工人政府”,是指革命勝利后不能同資產階級瓜分政權,不是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分配給工人幾個席位,而應由無產階級在政權中執掌領導權。他進一步解釋說,“人們可以把這樣一個政府說成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無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專政,甚至說成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但是問題仍然在于:誰在政府中掌握領導權,并通過政府領導全國,當我們說到工人政府的時候,這個政府的領導權應該屬于工人階級”。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對民主革命階段的論述雖有一定的正確成分,但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革命的“不斷性”,則充滿了極左的機會主義色彩。他完全否認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要侵犯大私有制,而且要侵犯小私有制,因此,無產階級必然會遇到來自農民的抵抗,同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沖突”,而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里,無產階級遇到的這個矛盾是克服不了的。他進而認為,社會主義是在一國開始的,但不能在一國完成,在一國范圍內維持無產階級革命只能是暫時狀態。在孤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各種內外矛盾必然隨之增加,最后必然會成為這些矛盾的犧牲品。他認為,一國的革命不是獨立的整體,它只是國際革命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國際革命是一個不斷的過程。
1907年2月,在押解赴流放地的途中,托洛茨基從別列佐沃又一次脫逃。此后,他在國外度過10年的流亡生活。最初僑居在芬蘭,曾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分出席4月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統一)代表大會,并出席8月的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同年10月,定居維也納。從1908年10月至1912年5月,在維也納創辦俄文《真理報》,這份報紙持中派立場,企圖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搞調和折中。在這個時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些領導人的賞識和支持,在他們的報刊《新時代》、《前進報》上不斷發表文章,歪曲俄國黨內斗爭的真相,混淆國際工人的視聽。為此,列寧嚴正聲明:“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國同志們說,他代表了‘整個黨的傾向’,那我就要聲明,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充其量也只不過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①
1912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拉格召開第六次代表會議,決定把孟什維克取消派②開除出黨,此后,布爾什維克便作為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出現在政治舞臺上。同年8月,托洛茨基糾集托派分子、孟什維克、取消派、召回派③和崩得④分子在維也納舉行代表會議,結成反布爾什維克的“八月聯盟”。這個聯盟的綱領不提民主共和國的要求,不提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和民族自決權的要求,實質上是一個隱蔽的取消主義的綱領。“八月聯盟”是一個無原則的集團,其主要宗旨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1912年1月布拉格代表會議。它是一個成分復雜,思想混亂的松散的政治團體。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認,“這個聯盟沒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八月會議是一次失敗的會議”,因而不久他本人也退出了該組織。1912年9月,應《基輔思想報》的約請,托洛茨基前往巴爾干擔任軍事記者。
在布拉格代表會議前后,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執。托洛茨基攻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篡奪者”,帶來了“仇恨和分裂的禍種”。列寧嚴肅地予以駁斥,并指出,“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國工人運動的人都知道,口頭上標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這就是派別活動”,托洛茨基就是“最壞的派別活動的殘余”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托洛茨基以中派主義面貌出現,口頭上承認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但又認為戰爭是世界經濟和民族國家的矛盾的產物,是民族國家的小框框容納不下高速度發展的世界經濟的結果。因此,他認為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戰爭本身,爭取和平。大戰爆發后,托洛茨基離開維也納去瑞士,不久到達法國,在巴黎主辦《我們的言論報》,這是一份帶中派主義傾向的俄文報紙。
1915年9月,托洛茨基和列寧、考茨基等一起出席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會議,并為會議起草反映中派觀點的妥協性的總宣言。1916年9月,《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政府查封,托洛茨基被驅逐出法國,途經西班牙前往美國。1916年底抵紐約,參加《新世界報》工作。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托洛茨基和其它流亡國外的革命者一樣,感到十分欣喜。3月,攜妻兒返國,途中被英國警方在加拿大戰俘營扣留1個月,至5月才回到彼得格勒。
回國后,托洛茨基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加入區聯派①。1917年夏天,區聯派成員進一步向左轉,聲明同護國派分子斷絕關系,主張“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贊同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關于托洛茨基當時的政治態度,據托洛茨基自己聲稱:“不認為我和布爾什維克的意見分歧全是我的不對,在對孟什維克派的估計方面是我不對,而且是根本不對。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計高了。”七月事變中,托洛茨基被臨時政府逮捕入獄。7月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定與區聯派聯合,托洛茨基被選為黨中央委員。9月初,他獲釋出獄,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10月,被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在斯莫爾尼宮具體負責十月武裝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并在指揮起義中作出了貢獻。
十月革命勝利后,托洛茨基擔任蘇維埃俄國外交人民委員。12月間,他作為蘇俄和談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國進行簽訂和約的談判。1918年2月10日,德方提出最后通牒,托洛茨基不顧蘇維埃政權的安危和列寧的正確主張,擅自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并聲明退出戰爭,全面復員軍隊。談判宣告破裂,致使2月18日德軍重新發動全線進攻,蘇維埃政權面臨極其危急的局面。俄共(布)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終于通過了列寧關于立即接受對德和約建議的決定。托洛茨基投棄權票。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列寧的正確主張,也不同于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拒絕和談、鼓吹革命戰爭空談的意見,堅持自己“不戰不和”的主張。由于托洛茨基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德軍重新發動進攻,使得蘇維埃俄國在損失更為慘重的條件下簽訂和約,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接受列寧的主張后,托洛茨基向列寧提出辭職。他說:“我的辭職對德國人來說,意味著政策上的急劇轉變,從而使他們深信我們這次真要簽訂和遵守和約的決心”。列寧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理由”,同意他辭去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任命他為軍事人民委員,即陸海軍人民委員,具體負責建設紅軍,指揮平定內外敵人的叛亂和武裝干涉。
從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國內戰爭期間,托洛茨基作為最高軍事指揮官,陸海軍人民委員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經常乘坐一輛軍用列車,到達前線,先后在東線、南線、西線指揮作戰,并在短時期內負責交通運輸的整頓和恢復。托洛茨基并沒有突出的軍事才能,在指揮中也有過不少失誤,但在那個年代里,他同全黨全國人民一起,對國內戰爭的勝利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20年11—12月間,托洛茨基挑起了一場關于工會問題的黨內爭論。他提出立即實現“工會國家化”和“勞動軍事化”等錯誤主張,歪曲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內工會的性質和任務,分散了黨對當前迫切的經濟恢復工作的注意力,助長了黨內的派別活動。列寧嚴肅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
1921年3月,俄共(布)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由軍事共產主義政策轉變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托洛茨基對實行新經濟政策是贊成的,然而他又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蘇維埃政權為克服面臨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采取的臨時措施,僅是一種權宜之計而已。他惶惶不安地宣稱:“二千五百萬小農戶是俄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根源。逐漸從這一大批人中出現的富農階層,正在重演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下埋藏了一個大地雷。”他把實行新經濟政策后逐漸活躍起來的市場經濟比喻為魔鬼,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流通、市場、貨幣,價值規律等一概視作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求人們高度警惕和嚴加限制。顯然,所有這些看法都帶有“左”的錯誤傾向,是同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設想迥然不同的。
1922年起,列寧開始患病。1923年3月,列寧臥病不起,不能視事。同年秋天,托洛茨基挑起了一場新的黨內爭論。10月8日,他給黨中央寫信,提出了反對所謂黨政機關內的官僚主義問題,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對斯大林。接著,10月15日,贊同托洛茨基觀點的46名負責干部上書中央政治局。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聲明》中,包含著許多武斷的錯誤的說法。10月底,黨中央召開會議,認為在目前黨面臨困難的時刻,應當避免全黨的大辯論。會議號召全面發揚黨內民主,批評了托洛茨基某些錯誤言行。會議決定不發表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聲明》,也不公布黨中央的決議。但托洛茨基沒有罷休,從12月8日起,他以《新方針》為題先后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所謂“老近衛軍蛻化”問題,影射老布爾什維克的蛻化,吹捧青年是“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托洛茨基《新方針》的發表,黨中央被迫宣布開展“全黨大辯論”。辯論結果,絕大多數黨員譴責托洛茨基反對派,擁護黨中央的路線。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作了爭論的總結,指出托洛茨基“具有十分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傾向”。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這年秋天,黨內又掀起一場“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大辯論。這場爭論是由托洛茨基寫的《論列寧》、《十月的教訓》兩本小冊子引起的。在這些小冊子中,托洛茨基在贊頌列寧的同時,吹噓和標榜自己,貶低黨在十月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他并且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期間的叛賣性行徑作了揭露,還不指名地批評了其他一些黨的領導人。此時,正當列寧逝世不久,誰來充當黨的主要領袖人物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在許多人看來,托洛茨基的兩本小冊子是一種信號,說明他懷有篡奪領導權的野心,妄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據此,圍繞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問題,報紙上接連不斷發表文章,聲討托洛茨基主義,保衛列寧主義。他本人則申辯否認,聲稱根本不存在什么“托洛茨基主義”。他說:“我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托洛茨基主義’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1925年1月,俄共(布)召開中央全會討論托洛茨基的反黨言行問題,全會決定解除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托洛茨基被解職以后,曾短期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電工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管理委員會主席。
1925年底,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同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多數派圍繞“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發生分歧。“新反對派”在較量失敗以后,遂于1926年4、5月間與托洛茨基結成聯盟。托季聯盟的出現,預示著黨內將有一場新的嚴重的斗爭。
托季聯盟提出了一條同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相對立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其理論基礎,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斗爭的中心問題,是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從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出發,他們認為,在俄國這樣原先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無法克服廣大農民即小私有者的反抗,無產階級必然會同廣大農民產生“敵對的沖突”、單靠一個國家無產階級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因此,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可能的。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可見,在此期間,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已成為反對黨的正確路線的思想武器,渙散、動搖著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和決心,成為一種危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錯誤理論。斯大林稱這種理論是一種“‘不斷’絕望的思想”,“前途‘不斷’黯淡的思想”,“不相信我國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領,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根源”。①
托洛茨基還從世界經濟聯系的角度“分析”說:“在生產技術方面,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代表比資本主義更高的階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圍內孤立地建設社會主義,那么,不管暫時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著把生產力拉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落后的境地。”據此,他誣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是“社會主義的門羅主義”觀點。與此相適應,他主張首先取得勝利的國家根據國內外經濟條件確定一個“最好的速度”,以便“準備未來的國際社會主義的民族因素”,并主張用“超工業化”等方法積累資金,即用剝奪農民的辦法來積聚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斯大林批判了托季聯盟的一系列荒謬論調,從理論上區分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最終勝利”的界限,論證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地進行經濟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托季聯盟在理論上帶有明顯的極左性質,在組織上搞派別活動,分裂黨的隊伍。托季反對派不斷挑起爭論,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不但從理論上進行揭露和批判,而且多次警告反對派首領放棄派別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等人時而氣勢洶洶,時而偃旗息鼓,斗爭時起時伏。1926年10月16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6人發表聲明,承認他們“多次采取了違犯黨紀,超出黨所規定的黨內思想斗爭范圍而走上派別活動道路的步驟”。
1927年5月以后,托季聯盟又接連提出《八十四人宣言》、《十五人政綱》、《反對派政綱》以及準備提交黨的十五大的反對派提綱,從而使黨內斗爭再度緊張起來。鑒于托季聯盟提出一系列不同政見,聯共(布)中央決定在黨的十五大召開前兩個月開展全黨大辯論。辯論結果是,全黨99%的黨員贊成黨中央的路線,支持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在這種形勢下,托季聯盟竟將黨內爭論訴諸街頭。192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日,托季聯盟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組織反黨的街頭示威,企圖用街頭示威來挽回黨內爭論中的敗局。這就使斗爭越出了黨內斗爭的范圍。1927年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將托洛茨基開除出黨。
1928年1月,托洛茨基由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押送流放到中亞的阿拉木圖。流放期間,托洛茨基繼續從事反黨政治活動。 6月,他撰寫《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提交8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并向大會提出恢復黨籍的申請,受到大會的駁斥和拒絕。在此期間,托洛茨基同國內外托派分子維持著廣泛的書信聯系。
1929年1月,蘇聯政府決定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國。2月,抵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僑居在馬爾馬拉海的普林吉坡島。1929年7月,主編出版《反對派通報》。1932年2月,托洛茨基被剝奪蘇聯公民權,開除蘇聯國籍。1929年至1932年間,他寫完《我的生平》、《俄國革命史》、《不斷革命》等書。1933年7月,移居法國,《反對派通報》改在巴黎出版,并開始醞釀建立“第四國際”。1935年6月,移居挪威。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定居墨西哥城郊科亞坎。1938年9月,“第四國際”(全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大會通過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的《過渡綱領》(全名為《資本主義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國際的任務》)。“第四國際”是一個國際托派組織,它打著“世界革命”的旗號,妄圖分裂各國共產黨,進行反對共產國際的活動,破壞國際工人運動,給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極大的危害。該組織成員極其復雜,內部派系之間矛盾重重。1939年6月,托洛茨基撰文紀念《反對派通報》創刊十周年。1940年2月,托洛茨基因患高血壓立下遺囑。5月,“第四國際”召開緊急大會,通過了《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科亞坎住所被一個名叫莫爾納爾的人行刺,8月21日因傷重而死。



上一篇:扎格盧勒
下一篇:托里霍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