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舊邦維新—康、梁的意義·從嶺南布衣到文化巨匠
康有為(1858—1927)突破傳統文化、發軔一代新文化的經歷頗具典型意義。
康有為從小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成童之時便有志于圣賢之學,言談不離“圣人”,由此得到一個半是期許半是揶揄的“圣人為”的戲稱。青年時期他又師從嶺南著名理學大師朱次琦。朱氏治學以程朱為主,間采陸王,治經則掃除漢宋門戶,而歸宗孔子。康有為求學門下三年之久,精研群學,博覽群書。“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目之睹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圣賢為必可期,以群書為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康南海自編年譜》)由此自述,可見這位良師的道德文章對青年康有為的深刻影響。素懷大志的康有為,正是在這里添加了人生旅途的許多動力,堅定了以圣賢自期許、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
辭師返鄉后,他一度讀書西樵山。在這里,他因緣得交同鄉京官張鼎華。張氏博聞強識,神鋒朗照,熟習朝政掌故,談詞如云。同他的交往使康有為開始接觸近代維新思想,眼界為之一擴,越過南粵一隅。對于這位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康有為充滿感激之情,將其視為自己人生道路上又一接引使者。“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圣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康南海自編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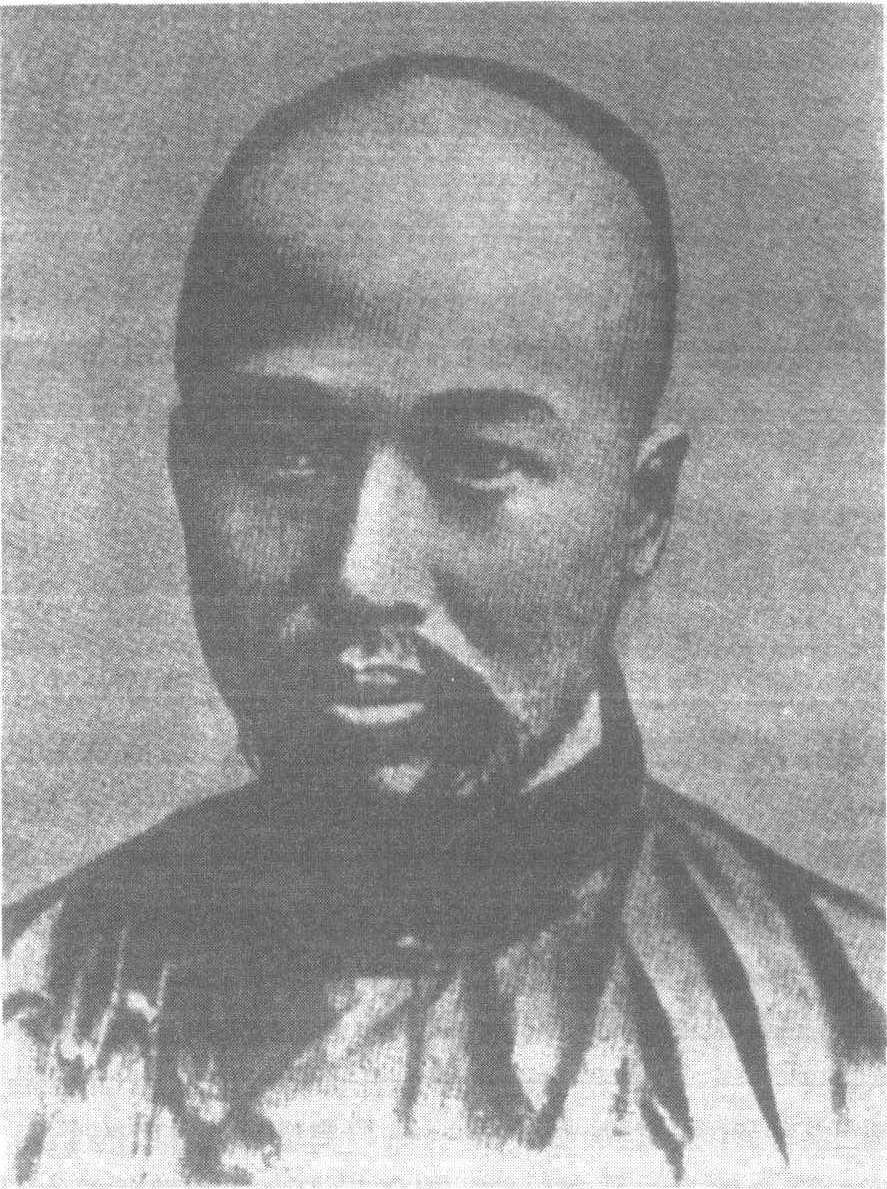
康有為像
“世界開新逢進化,賢師受道愧傳薪。”(康有為《蘇村臥病寫懷》)良師益友的激勵和國家民族憂患,加強了他重任在肩的使命感。他由此開始了長達十年(1879—1888)的澹如樓家居讀書生活。在這一階段,他雖仍參加鄉試,卻已斷然舍棄考據帖括之學。他決心以經營天下、拯救民生為職志,故而在潛心古近有關“經緯世宙之言”的同時,以異常高漲的熱情攻讀西方政教史地和聲光化電等書。為了印證所學,他還“薄游香港”,實地考察西方政教施行情況。這階段他讀書收獲很大,進境甚猛,開始精心思考并構筑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他自述此時“獨居一樓,萬緣澄絕”,俯讀仰思,新識精理,日有所進。“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后來,……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舍身命而為之。”(《康南海自編年譜》)然而,這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追求,并未真正找到救世之途和醒世之方。“憂患百經未聞道”(《澹如樓讀書》)的感喟,反映了此際的苦悶心態。
1888年,張鼎華招游京師,他再次北上兼應順天鄉試。此次場屋之文雖然未售,但他激于中法戰后日蹙的國勢,毅然“發憤上萬言書,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卻引起了強烈反響。守舊派一片嘩然,有識朝臣則對其頗為垂意。不能不說康有為以一介布衣之身在中央政治舞臺上作了一次成功的亮相。
這次上書最終未達帝聽,由此使他深感要沖破封建壁壘實現變法,除向西方文化學習,還須從傳統文化的理論武庫中尋找有力武器,從壁壘內部攻起。1890年他與著名經學家廖平的羊城之會,為他提供了鍛造救世之具的絕好機會。廖平一生經學思想歷經六變,與康有為相會時,正值其第三變。此時他著《今古學考》,持“尊今抑古”之論,即主張今文經是孔子的真學,古文經是劉歆的偽品。受廖平啟發,康有為異境頓開,認定今文經學的“三統”、“三世”說是一種適合國情能為士大夫所接受的合法形式。一番苦覓,康有為終于為維新變法找到了“托古改制”這一件符合法定的傳統經典的文化外衣。作為絕大紀念的直接成果,便是《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的迅速問世。
與此同時,另一直接成果—萬木草堂文化基地開始奠立。1891年,他開堂于廣州長興里,手訂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康南海自編年譜》)。萬木草堂到戊戌政變時被封禁,前后歷時八年,就學者超過百人。除因事離開,康有為始終堅持在堂親自授業。他升座講學,每論評一事,必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再引歐美以比較證明,然后宣示自己的見解。這種聯系實際開拓知識視野的新型教育方法,十分有利于培養有用之才。萬木草堂很快成為一個具有很濃政治色彩的新文化集團。“萬木森森散萬花”、“萬木森森萬玉鳴”,康有為的賦詩直表意趣所在。他之在此搴蘭攬芷,刻璇雕瓊,意在造就一代新人,以期開放萬千維新之花,引鳴萬千學術之玉。
在自己的著作中,康有為成功地借重孔子的微言大義,以宣傳“托古改制”的合理性。在自己的文化基地,康有為更以當代孔子自居。他自號“長素”,有長于“素王”(孔子)之意。而萬木草堂那些高材捷足,也豪氣干云,不甘落后,紛紛以超越孔門圣徒的雅號相稱。如陳千秋為“超回”(顏回),梁啟超為“軼賜”(子貢),韓文舉為“乘參”(曾參),曹泰則為“越伋”(子思)。
至此,一名嶄新的文化巨匠和一個新型的文化集團已呼之欲出。
倒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守舊派對此嗅覺特靈。《新學偽經考》一落地,他們便從中聞到了濃烈的異端氣息,為此指責康有為“言偽而辨,行僻而堅”,“煽惑后進,另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風,從游甚眾”,較之當年少正卯有過之無不及(蘇輿輯《翼教叢編》卷二)。當中日戰爭戰云密布的1894年8月,守舊言臣強烈要求嚴厲懲治“非圣無法,惑世誣民,圣世不容”的康有為,即行焚毀《新學偽經考》。于是,作為國家干城的北洋艦隊和作為變法理論的書版幾乎同時付之一炬。這真像是對“圣世”的絕妙諷刺和因果報應。只是前者毀于鷹瞵虎視的外人之鐵甲,后者敗于鼠目獐眼的朝臣之刀筆。
馬關議和后,康有為一方面通過上書皇帝、代擬奏折或進呈著作,在上層用力;一方面又通過創辦報刊、組織學會或開辦學堂,在下層用力。這些順應時勢而又合乎人心的努力,終于使維新變法運動很快步入高潮。時代風云的激蕩和文化思想的匯積,又終于使康有為很快升上一個顯耀的地位。這位嶺南布衣一躍而為帝師王佐式的政治領袖和傾動一世的文化先驅,當戊戌變法高潮到來之際,他才剛剛進入自己的“不惑”之年。



上一篇: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天朝上邦—道統之華裔觀·從“中體西用”到“復興儒學”
下一篇:宋明理學·鬼神新解·以“氣靈論”解釋“神仙”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