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食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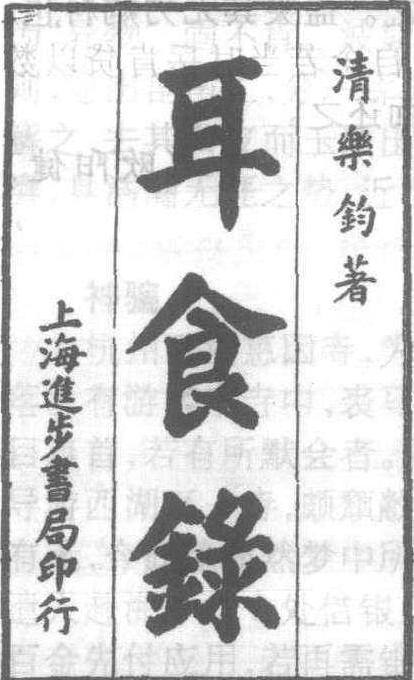
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石印本《耳食錄》扉頁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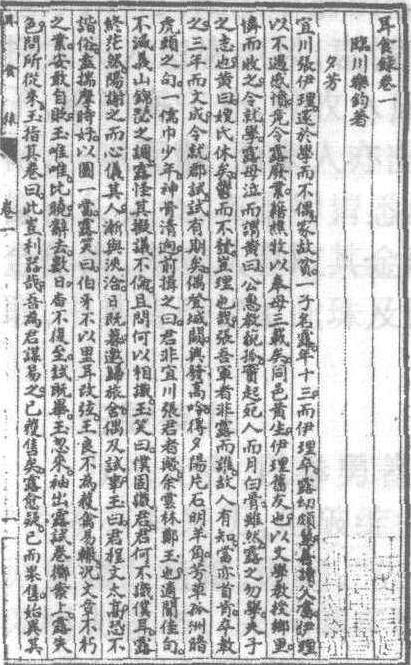
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石印本《耳食錄》正文書影
清代文言短篇傳奇小說集。初編十二卷一百十二篇,二編八卷九十七篇。題“臨川樂鈞著”。作者樂鈞(1766—1817?),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別署夢花樓主,江西臨川人。成書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現存主要版本有清夢花樓刊初編本;清道光元年(1821)青芝山館兩編合刊本;清同治七年(1868)藏修堂刊本;清同治十年(1871)敦仁堂刊本;清同治十年(1871)味經堂刊本;民國上海文明書局“清代筆記叢刊”石印本;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石印本。1986年岳麓書社排印本,1987年時代文藝出版社“聊齋志異叢書”排印本,1995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說大觀》影印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耳食錄》為作者之“早年綺語”,事多出于兒女纏綿,仙鬼幽渺,間以里巷諧笑,助其波瀾。吳山錫在序中說:“其事之怪怪奇奇,固足賞心駭目,而文章之妙,如云霞變幻、風云離合,其悲壯激昂者,真可敲缺唾壺;其纏綿婉麗者,又令人銷魂欲死。”約略得之。從神怪小說的演變史看,樂鈞的出色之處在于他堪稱一位心理小說家。《鄧無影》講的是人和自己影子的對話,以及其后親密相處的故事,將人在孤獨寂寞時的自我安慰,以及所導致的精神分裂,用形影相親的極端怪誕的形式表達出來,構思奇特。又如《章琢古妻》,講的是人因對異物的某一狀況而產生的艷羨之情,遂頓生異化的故事,同樣體現了樂鈞擅長心理刻劃的特點:林甲素有心疾,心之所向,魂則隨之。他仰視飛雁,見其翱翔自得,頓生凌云之想,便變成了雁,即與群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忽有弓彈飛來,為其所中,昏痛之際,倏已魂返。又因臨淵羨魚,其魂遂被引入水晶之宮,變成了魚,遂與蝦蟹共戲萍藻,游泳清灣,依躍淺池,然苦饑無食,竟為釣餌所誘,被刃之際,即便驚醒。甲因自思,一心之動,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湯火之苦,絕不敢生歆羨想,然而化龜化鶴化牛化犬,仍不一而止,所化無不被禍,被禍乃得返。
在寫人與異物的關系方面,《耳食錄》也有豐富的內涵。如《綠云》,敘劉生故樸訥,其父嘗蓄二鸚鵡,一母一雛,一日悲鳴求去,劉憐而放之,遂得到了“神悟頓開,喉舌亦便利,無復期艾之苦”的報答。
《耳食錄》亦頗多正視現實之作。《上官完古》,敘上官夜行,聞荒鬼之哭,問之曰:“何哭聲之多也?”眾鬼遂向其歷訴地方官長“貪殘如狼虎”的罪行。《東岳府掌簿》敘某仕宦之子暴死,夢其子轉托其在東岳府掌簿之張公,得免皂役之苦,父思張為至交,些須之求,庸必賄乎? 不以賄往,其子反而受到張公加倍的責罰,雖在陰間,賄賂請托之風仍不能免,都是揭露政治的黑暗與窳敗的佳作。
《耳食錄》中敘寫愛情的故事,一般多具哀惋纏綿的情致。《秋心山人》,敘余玉簪與表兄呂生自幼相愛,及長,不得志于嚴父,懨懨待斃。呂生聞有秋心山人者,能前知,因往卜之。秋心山人言其二人尚有一見之緣;若忍而不見,可延三年之壽,呂生乃曰:“吾寧憚速死,而割于彼美乎?”卒往見之,乃作詞一闋,投筆而死。“秋心”者,愁也。《女湘》敘金湘前世為士人子,生時有骨橫其胸,有道士相之,謂為情骨,無他慧,雅善傷心,苑有海棠,愛護備至,花落,必泣于樹下,父疑花之祟也,伐之,湘大慟而絕。其魂至一大第,有夫人出,命侍者導至曲房,一女子坐榻上。其夜,湘枯坐枕端,為女覆蓋蔽光,斂衣屏息,惟恐擾其清夢。次晨,女覺而起,問何無丈夫氣,對曰:“得聞薌澤,于愿已足;臣之好色,不在床笫間也。”女微笑唾之,湘急承以襟,須臾成一海棠,蓋女子即海棠,感其同死,愿生生死死作多情物,二人遂托生為海棠、桃花。
鄧無影
鄧乙年三十,獨處,每夜坐,一燈熒然,因顧影嘆息曰:“我與爾周旋日久,寧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從壁上下應曰:“惟命。”乙驚甚,心少定,曰:“吾以孤棲無偶,欲一少年良友,長夜晤對,可乎?”影應曰:“何難。”即已成一少年,鴻騫玉立,傾吐風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貴人。俄頃,少年忽成官長,衣冠儼然,踞床中坐,乃至聲音笑貌,無不逼肖。乙戲拜之,影又化作少女,容華絕代,長袖無言。乙即與同寢,無異妻妾。由是日晏燈明,變幻百出,罔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他人不見,惟乙見之,如醉如狂,無復常態。人頗怪之,因詰而知之,視其影,果不與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以問乙,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一鄉之人,咸以為妖焉。后數年,影忽辭去,問其所之,云在離次之山,去此數萬余里。乙泣而送之門外,與之訣。影凌風而起,頃刻不見。乙以是無影,人呼為“鄧無影”。
張將軍
明季有張將軍者,嘗駕大舟出海捕盜。有少年書生厚賂舟人,求附舟,舟人利其金而納之。為將軍索得,書生自陳非盜,欲之海外省父。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出風入雅,將軍自謂得書生晚。一日,談及捕盜之事,書生曰:“盜可撫,不可捕也。”將軍自夸節制一方,揚威千里,區區海盜,何足道哉。書生乃夸耀海盜之能,將軍問:“汝何知之?”書生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乃取篳篥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涌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聊與將軍戲耳。”復吹篳篥數聲,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魂者累曰,自是不復捕盜。
紫釵郎
馮生于郊外遇一美人,倚門斜盼,如有所待,邀之入,自言名紫釵郎,其族納婿,均謂之“新婦”:“卿宜郎我,勿得卿我;我乃得卿卿。”生笑頷之。紫釵乃向壁中喚出二青衣,生大驚,知非人矣,初甚畏怖,后漸狎之。又有諸美人自壁中出,賀紫釵得佳婦。生頗羞慚面赤,儼然如新婦之靦腆者,置身羅綺間,而為眾所播弄,神氣沮喪。居半載,亦能行壁中無礙。一日,忽思歸,諸女慘怛惆悵,執手嗚咽。至家,妻見之,若不相識,將欲走避,生乞鏡自照,宛然好女也,急白其故,妻不之信。居數日,往訪紫釵,仙村人面,俱不知何處所矣,欲再求阿郎呼己作新婦,了不可得,感疾迷離,數月而卒。
章琢古妻
林甲素有心疾,心之所向,魂則隨之。一日,仰視飛雁,見其翱翔自得,頓生凌云之想,便有人引至雁群中,持羽衣衣之,即與群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忽有弓彈飛來,為其所中,昏痛之際,倏已魂返。又因臨淵羨魚,其魂遂被引入水晶之宮,持魚服服之,遂與蝦蟹共戲萍藻,游泳清灣,依躍淺池,然苦饑無食,竟為釣餌所誘,被刃之際,即便驚醒。甲因自思,一心之動,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湯火之苦,絕不敢生歆羨想,然而化龜、化鶴、化牛、化犬,仍不一而止,所化無不被禍,被禍乃得返。后林甲偶見友人章琢古之妻,心驚其艷,一日略記憶之,其魂離散,直至章家,見其妻病死,即憑之而起,與章琢古相處數月。章見其妻死而復活,親愛有加,但性情嗜好,聲音舉動,均不類向時,且時束帶加冠,如男子容狀,章頗患之。數月后,向章說明真相,章聞其向有是疾,信其言之不謬,而自此以后,甲疾頓愈,蓋心疾須用心藥醫治故也。
胭脂娘
王氏家藏名書寶畫,中有美人一幅。王氏子韶,每注畫神移,向壁癡語,乃題二絕于幀首。父死,家稍落,畫為無賴所竊,不知流落誰手。王韶館于許氏西齋,一夕有紅裳麗女倚而招之,自稱胭脂娘。次夜又偕兩女曰絳花、云碧來,繾綣而去。次夜,絳花又送粉憐至。四女恍然熟識,終不記曾遇何所,問之,但云郎向贈以珠玉,何乃忘之?韶懵然不覺,亦不深究。一夜,四姬并至,曰緣分盡矣,驚問其故,不肯言;又問此后猶得相見否,則曰在相見與不相見之間。次日,主人招飲,忽見東齋懸向所題美人圖,而卷中人儼然所遇四姬也,不覺凄然淚落。主人知其本末,以畫贈之。韶拜謝攜歸,供之于衾帷之側,而楚楚相對,卻無甚動靜。韶自是感疾,味青蓮詩曰:“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遂大慟而卒。
綠云
劉生之父嘗蓄二鸚鵡,一母一雛,并能言。一日悲鳴求去,劉憐而放之,系以金戒環,而約之曰:他日倘相見,以此為信。劉生故樸訥,假館鄉僻,為童子師。夏夜迷路,為人導入山間巨宅,一老婦稱:“向別尊府,君猶總角。”劉不知所對,老婦遂強留其為西席以教其二女綠云、素云。二女天穎并絕,間摘奇字叩劉,劉莫能答。一日,素云從劉授書,背誦如流,劉戲拍其背,遂暗啞。劉惶恐求去,老婦乃命綠云脫金約指付劉曰:“此君家故物,今特歸趙。”臨行,以酒飲之,劉神悟頓開,喉舌亦便利,無復期艾之苦。
何生
何生富而好義,嘗客金陵,見一少年客居西室,衣甚襤褸,曲突無煙,間饋之金錢周濟之,客不辭亦不謝。后竟去,所饋錢悉在床下青囊中。未幾,何為人所誣,被迫離家出走,南游于楚,途遇猛獸,得一女子飛騎來,逐之而去。何不得返,獨宿野廟中,聞笛聲悠揚,且聽且行,投一甲第,主人乃即金陵所遇之人,且云日間為驅猛獸者即己也。何大驚,呼為神人。蓋女子本紫蘭宮捧劍使者,因舞劍誤傷守宮之鶴,謫墜世上,雄服游戲人間,以貧自晦,感何助己,遂亦以飛劍斬里人及縣官以相酬。二人遂為夫婦。后至瓜代之期,大慟而別。
癡女子
一癡女子,從其兄案頭搜得《紅樓夢》,廢寢食讀之。讀至佳處,往往輟卷冥想,繼之以淚,復自前讀之,反復數十百遍,卒未嘗終卷,乃病矣。父母覺之,急取書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寶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語無倫次,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延巫醫雜治,百弗效。一夕瞪視床頭燈,連語曰:“寶玉寶玉在此耶?”遂飲泣而瞑。



上一篇:《綠野仙蹤》介紹|賞析
下一篇:《聊齋志異》介紹|賞析